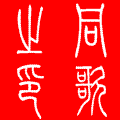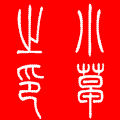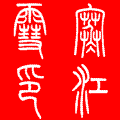这个月初是我的生日,女儿为我祝寿,在酒店备一席,席间女儿频频举杯,祝福老爸健康长寿!侄女乐儿也凑热闹干了一杯,其乐融融仿佛又年轻了许多。看着他们不免回忆孩提时代的女儿、侄女儿的许多童趣来。
侄女乐儿突然若有所思的的说;那时姑爸爸特别喜欢闻我们的头发,每次回来我都是第一个跑去让你闻,有一次姐姐比我跑头我心里还不高兴呢!是的吗?怎么不是的,女儿随声附和着,引来人们的一阵欢笑。确有其事!确有其事!笑语间让我回忆起安乡的一段往事来。
乡下的日子最难过就是“双抢”季节,田多人少300多亩田全部要在20多天抢收抢种,不死都要脱层皮。我的双手和双脚因稻田皮炎队长看了过意不去,便让我去禾场晒谷。说起来轻松在干岸上做事,殊不知毛谷上岸要清扫扒开、翻晒、转堆、车谷、进仓。禾场只有两个男劳力,顶着烈日白天没有休息。晚上还必须风车车谷进仓,一般都要车两遍才能进仓。
人数不够队长就让拖累妇女张满婶来禾场帮忙做我的下手,谷堆开堆、拢堆要两个人。我在前面背满婶用双手掌着铲板,将谷堆扒开或聚拢。
满婶为人老实话也不多翠妹子是她女儿,人精瘦40开外,笑起来满嘴歪七例八的黑黄牙齿显露出来。手脚倒还麻利,无论我有多快她都能跟上。最难受的是满婶的头发,当时乡下妇女经常洗头的不多,一个双抢季节汗流夹背,不洗头发怎么受得了。满婶就是这样的人,在禾场开谷堆总是一前一后,我处在上风头还好一点,如果我在下风头,满婶她那头发散发的味道真让人难受。只有屏住气猛跑上风头吐气,真想告诉满婶要勤洗头发。可我望着老实巴焦的她总不好意思开口。我只好每天代上清凉油抹在鼻子下,在空气污染的禾场里干了十几天。至今都落上一个毛病生怕头发出现那种奇异的怪味!
女儿刚3岁时,和她亲吻总忘不了要闻她的头发,侄女乐儿也是检查之列。难怪他们把儿时记忆归纳到我这有“怪癖”的老头身上了。
唉!离开安乡已有几十年了,原来社员们家里一支牙刷全家轮流用,一条洗脸毛巾也是全家轮用,上厕所就用草杆子,这些陋习也随知青的到来而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