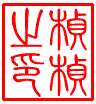去年此时,央视在黄金时段播放了一部连续剧《铁色高原》。编剧是丈夫的战友何署坤,他当年随铁道兵参加了成昆铁路的建设,凭这段生活创作了这篇小说。我一集不落地看完这部连续剧,好几次回头问也在全神观看的丈夫“真实啵?”“真实咧!只是我们在北方修铁路还苦些。”
丈夫内敛,平时从不看那些花花草草的言情连续剧,只说那是文人写来赚我们这些女人眼泪的。他只看新闻和体育节目,有时看看动物世界和探索。这次破天荒看完了这个剧,而且赞同我买回影碟收藏起来。
儿子回家,我们又把这碟放了一遍。起初,儿子不大感兴趣,后来见父亲这样投入,有些诧异才站着看了一集,到第二集时父子俩就坐在一起看了。儿子也像我一样向父亲询问关于真实与否的问题,而父亲则少有的打开了话匣子。甚至还时不时请我来佐证他的叙述。
丈夫是72年的兵,起初在铁道兵十四师,一当兵就去了修建河北境内承隆铁路的工地,后来又去了修建从北京沙城到吉林通辽的“沙通铁路”的工地。大学毕业后回到军队,仍然在工地上做事。后来因为辅导战士高考成绩斐然,被发现具有当教员的潜质而被调动到铁道兵学院才离开了工地。
我初识他时,他可不似后来乃至今天的康健。黑瘦,军装挂在高高的个子上有些飘扬,左腿总有些疼痛,这使他在与我散步时因为跟不上我而有些狼狈。我的女伴都笑称我找个解放军叔叔,其实他也只大我四岁。腿疼不说明他的羸弱,乃是铁道兵给他戴上的符号。他大学毕业到工地上当技术员,总在隧道里做现场,一呆就是半年以上。战士轮换了几拨,而他却仍在里头。风湿上了身,有时出隧道都困难。与我结婚后七八年这风湿才见好。他说,这又不奇怪,铁道兵的工程技术人员没有一个不患风湿的,许多战士也不能幸免,“这是老铁的专利”他总这样自嘲。
我第一次去他的住所,好快就找到了他的房间,因为他在门上贴了一幅宣传画。“你可别小看这张画,我每次看都想哭呢。”我望了一眼眼前这个男人,自然没真的哭的表情,但认真是真的。这画上是一个背着镐,戴着安全帽的战士,战士的脸上是豪迈的笑容。战士的身后是挺峻的群山。我没看出什么令人要哭的内容,便用了询问的眼神去看他。“你再看,看下面的字。”我这才注意到下面一排血红的黑体字:逢山开路,遇水架桥,铁道兵面前无险阻!“这字是用铁道兵官兵的血写的!”遇上隧道塌方,埋了一个班的战士,而隧道施工却不能停下来。铁道兵,就是穿上军装的民工,又是穿着施工服的敢死队。修建全国四分之一的铁路,全是桥梁隧道,全是普通人打不下来的攻坚战,全是用军令作保证的任务。扑向风雨,扑向恶浪,扑向沙漠,扑向人迹罕见的荒蛮,把铁路伸向不毛之地,插进坚石固壤之中,镶嵌于悬崖峭壁之间,跨越在波涛汹涌之上…….不是无险阻,乃是用牺牲来平了险阻,无怪这七尺男儿要哭!
“你看那些老领导,老工程师,哪个不是孩子东一个,西一个。”因为修铁路流动性大,调防频繁,来不及给孩子转学,待到转好,又得开拔。所以只好把孩子留在当地。“老铁的孩子取名也有特点,有叫成昆的,有叫承隆的,有叫涛生的,有叫岩难的,还不都因为铁路?”
丈夫(当时是男朋友)说他想哭却没哭,而我有一种想哭的感觉。
待到百万大裁军时,铁道兵全建制下放地方。千千万万的铁道兵官兵一夜之间脱下军装,好多人都泣不成声。当时任天津市长的李瑞环将所有参加引滦入津工程的铁道兵官兵在天津安置,成为至今还流传在老铁们口中的佳话。
“我真的不后悔我当了铁道兵,国家的大动脉上有我流的汗!”第二次看完《铁色高原》,丈夫由衷的这样说,我和儿子都情不自禁的抱了一下这个难得这样激动的已不是军人的军人。
青年歌手谭晶深情的歌唱好几次让我动容:真正的男儿,你选择了军旅。痴心的女儿这才苦苦相依。世上有那样多的人离不开你,我骄傲,我是军人的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