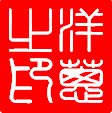一本禁书
那年,1969年,下放靖县的第一年,有一本书在铺口部分知青中悄悄的传阅着,喜看书的知青们踊跃排号等着借这本书看,预约的已有好几十人了,分布在公社各大队里,这是一本什么样的书?为什么能这么吸引着知青的眼球?这本书就是《十日谈》。
当时在知青中的书友们流传过这样的话:蒋介石的国民政府禁淫秽书籍时,中国的书禁《金瓶梅》;外国的就禁《十日谈》。从现在的眼光来看,这是给该书作的最好的广告宣传,《金瓶梅》我们都知道是中国第一大淫书,而《十日谈》这本书却听都没听说过,既然与《金瓶梅》齐名,又被蒋介石列为国外第一黄色小说,那这书无疑吸引住知青门的眼球,吊起了知青们的胃口。还听说湖南师院若大的图书馆都还只有一本,就觉得该书更神秘,更好奇了。
可喜的是,湖南师院馆藏的这本《十日谈》已“转移”到我们铺口的木山大队Z小组手中,由他们来“保管”了,这怎么不叫人翘首以待?所以铺口知青中的书友们听到这佳音,纷纷上木山朝拜,乞求一阅,但大都碰到了一鼻子灰。此书如此珍贵,Z小组从不轻易示人,要经过他们的“政审”,确认是他们信得过的人,才能看上一眼,然后再把你列人到借阅人员名单中,请你排队等候。如不采取这甄别措施的话,此书说不定早被公社没收了。话也说回来,仍有大部分知青不知道这本书的,很多连这书的名字都没听说过,更不用说那公社干部了,只有书友们才留心这本书的。
大概是十月后,这本书终于传到了我们同乐大队,说是我们大队,其实只限于寨合的新寨、龙家、王家三个队,我还没被列入到名单之列,因我所在的舒家离公社太近了,怕走漏风声被公社干部知道,故被排除在外。即使在那三个队里还限定到人,那就是他们所了解的人,还规定时间,限期内一定要还的。
书是由新寨的张英杰出面借下山的,由他负责安排此书的传阅,规定一人只能看两天,我与他及王家的吴元龙同为来往密切的书友,为能顾及到我能看到,经张英杰默认,吴元龙毅然将他的两天的借阅期缩短为一天,把那一天让给我看,但要求我必须按时送还,不得给他人看,我满口接应,我自认为看书的速度是较快的,一目十行不成问题的。
通知我去拿书的那天,一收工我连晚饭都顾不上吃,就赶到三里多外的王家生产队,从吴元龙手中接过这本书就掉头归队,一路上我我借着暮色翻阅着这本书,厚厚的一本书大概有四五百页,里面还有不少的插画。我原以为此书是解放前发行的直行繁体字的书,那看起来有点费力,想不到是五十年代的横排简体字版的,那更方便读了,捧着这本想往已久的书,心中一阵喜悦,一溜烟的跑回了舒家。
回到房里,迫不及待的就边吃晚饭边翻开书来看,刚看了个开头,就有点失望,这是十个人讲十天的故事,那不与 “天方夜谈”差不多,全是短篇,我喜欢看的是大本子的长篇小说,那情节曲折、引人入胜,才对口味。
晚饭后我赶快洗嗽完毕,在床头挂上马灯,坐在床上就看起书来了,说是一天的时间,其实就只一晚上的时间,白天是要出工的,不抓紧时间是难以看完。头几篇故事还一般,但看到那篇苦僧侣“将魔鬼打入地狱”的故事时,脸红心跳,有种莫名其妙的兴奋感,果真这本书不寻常,有内容、有看头。在好奇心的驱使下,我精神来了,一篇篇的故事飞快的看了下去,时间也在飞快的流逝,对面床的小H什么时候睡去的我也不知道。我只觉得坐在床上腰酸背痛,脖子都伸不直了,就换一个姿势坐在床沿上,将双脚落地,把被子披在身上,继续捧着看。这种姿势坐久背驮累了,又折回床上坐,背靠着床档看,来回折腾着。
那晚我思想高度集中,没有一点磕睡,完全被那本书吸引住了,到第一声鸡鸣时,还有三分之一没能看完,为了第二天能出工,我忍痛割爱熄灯睡觉,但缩在被子里怎么都睡不着,闭上眼睛,那书中的故事情节闪电般的在眼前晃动着,叫我无法合眼,干脆又爬起来,点灯披衣我又打开书来看,不看完不心甘。这回我就有挑选的看了,精彩的我就看仔细点,一般的故事,我就一扫而过,囫囵吞枣,就这样在晨曦到来时我看完了最后的一篇故事,依依不舍的放下这本书,揉着熬红的双眼,拖着疲惫的身躯去出早工了。
那时,是文革最嚣张时期,在所有的小说都遭禁止,在连爱字都不许提的的那个年代里,《十日谈》这本书不譬如是颗重磅炸弹,震撼着我那颗年青的心。
那年,1969年,下放靖县的第一年,有一本书在铺口部分知青中悄悄的传阅着,喜看书的知青们踊跃排号等着借这本书看,预约的已有好几十人了,分布在公社各大队里,这是一本什么样的书?为什么能这么吸引着知青的眼球?这本书就是《十日谈》。
当时在知青中的书友们流传过这样的话:蒋介石的国民政府禁淫秽书籍时,中国的书禁《金瓶梅》;外国的就禁《十日谈》。从现在的眼光来看,这是给该书作的最好的广告宣传,《金瓶梅》我们都知道是中国第一大淫书,而《十日谈》这本书却听都没听说过,既然与《金瓶梅》齐名,又被蒋介石列为国外第一黄色小说,那这书无疑吸引住知青门的眼球,吊起了知青们的胃口。还听说湖南师院若大的图书馆都还只有一本,就觉得该书更神秘,更好奇了。
可喜的是,湖南师院馆藏的这本《十日谈》已“转移”到我们铺口的木山大队Z小组手中,由他们来“保管”了,这怎么不叫人翘首以待?所以铺口知青中的书友们听到这佳音,纷纷上木山朝拜,乞求一阅,但大都碰到了一鼻子灰。此书如此珍贵,Z小组从不轻易示人,要经过他们的“政审”,确认是他们信得过的人,才能看上一眼,然后再把你列人到借阅人员名单中,请你排队等候。如不采取这甄别措施的话,此书说不定早被公社没收了。话也说回来,仍有大部分知青不知道这本书的,很多连这书的名字都没听说过,更不用说那公社干部了,只有书友们才留心这本书的。
大概是十月后,这本书终于传到了我们同乐大队,说是我们大队,其实只限于寨合的新寨、龙家、王家三个队,我还没被列入到名单之列,因我所在的舒家离公社太近了,怕走漏风声被公社干部知道,故被排除在外。即使在那三个队里还限定到人,那就是他们所了解的人,还规定时间,限期内一定要还的。
书是由新寨的张英杰出面借下山的,由他负责安排此书的传阅,规定一人只能看两天,我与他及王家的吴元龙同为来往密切的书友,为能顾及到我能看到,经张英杰默认,吴元龙毅然将他的两天的借阅期缩短为一天,把那一天让给我看,但要求我必须按时送还,不得给他人看,我满口接应,我自认为看书的速度是较快的,一目十行不成问题的。
通知我去拿书的那天,一收工我连晚饭都顾不上吃,就赶到三里多外的王家生产队,从吴元龙手中接过这本书就掉头归队,一路上我我借着暮色翻阅着这本书,厚厚的一本书大概有四五百页,里面还有不少的插画。我原以为此书是解放前发行的直行繁体字的书,那看起来有点费力,想不到是五十年代的横排简体字版的,那更方便读了,捧着这本想往已久的书,心中一阵喜悦,一溜烟的跑回了舒家。
回到房里,迫不及待的就边吃晚饭边翻开书来看,刚看了个开头,就有点失望,这是十个人讲十天的故事,那不与 “天方夜谈”差不多,全是短篇,我喜欢看的是大本子的长篇小说,那情节曲折、引人入胜,才对口味。
晚饭后我赶快洗嗽完毕,在床头挂上马灯,坐在床上就看起书来了,说是一天的时间,其实就只一晚上的时间,白天是要出工的,不抓紧时间是难以看完。头几篇故事还一般,但看到那篇苦僧侣“将魔鬼打入地狱”的故事时,脸红心跳,有种莫名其妙的兴奋感,果真这本书不寻常,有内容、有看头。在好奇心的驱使下,我精神来了,一篇篇的故事飞快的看了下去,时间也在飞快的流逝,对面床的小H什么时候睡去的我也不知道。我只觉得坐在床上腰酸背痛,脖子都伸不直了,就换一个姿势坐在床沿上,将双脚落地,把被子披在身上,继续捧着看。这种姿势坐久背驮累了,又折回床上坐,背靠着床档看,来回折腾着。
那晚我思想高度集中,没有一点磕睡,完全被那本书吸引住了,到第一声鸡鸣时,还有三分之一没能看完,为了第二天能出工,我忍痛割爱熄灯睡觉,但缩在被子里怎么都睡不着,闭上眼睛,那书中的故事情节闪电般的在眼前晃动着,叫我无法合眼,干脆又爬起来,点灯披衣我又打开书来看,不看完不心甘。这回我就有挑选的看了,精彩的我就看仔细点,一般的故事,我就一扫而过,囫囵吞枣,就这样在晨曦到来时我看完了最后的一篇故事,依依不舍的放下这本书,揉着熬红的双眼,拖着疲惫的身躯去出早工了。
那时,是文革最嚣张时期,在所有的小说都遭禁止,在连爱字都不许提的的那个年代里,《十日谈》这本书不譬如是颗重磅炸弹,震撼着我那颗年青的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