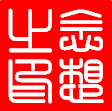我与清宇自小在一个院子长大,小学同年级不同班,中学同年级又同班,.下农村是同年同月又同日.我们的父亲解放前就是同事,由于战乱,分开了十来年.鬼使神差,后来又凑在一起做了同事.因此,我们也算得上世交.
但是,我们真正的交往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我们一起加入了一个高校造反组织的附属红小兵.也参加了一些”革命活动”,比如帮大哥哥们发传单:站在中山路百货大楼顶层,把折叠好的传单抛撒下去,然后兴奋地看着底下人头攒动,又从容不迫地把书包藏衣服里的腋下,平静地与那些气喘如牛的,五高武大的对立组织的打手擦肩而过;又比如,我们一起步行串联到过韶山,虽然用现在的眼光看,路并不遥远,可是,当时我们那支队伍大的不过十五岁,小的却只有十岁.那还是相当吸引眼球的.我们一路高歌,向围观的人发传单,读报纸,煞有介事.去时的路上还不觉得,回来的时候,也许是因为想家,竟然一口气走到了暮云市,那已是次日凌晨了,一辆过路的汽车看见我们东倒西歪的样子,强行把我们带回长沙.
我们那叫战斗的革命友谊.
后来我们”逍遥”了,又一起去推板车.不是好玩,正儿八经的,他十八块钱一个月,我十六.也不是缺乏生计,清宇讲:他们{拖板车的}好复杂地.
一干半年有余,我们真的懂事不少.我与清宇,野,悌号称要 敮血为盟结拜为兄弟.但是有贼心无贼胆,一直没有搞到公鸡,血酒没有喝,兄弟倒是做了一阵.
复课以后,那时候的中学是英雄烽起,诸候称霸.我们在其中倒也相安无事.
我们那叫哥们义气.
四十多年过去,往事已淡如波痕,亦幻亦真,但有一件事我却宛如昨日,刻骨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