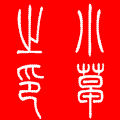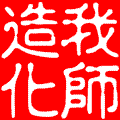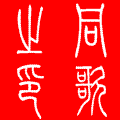由《我的西游记》《我的西行漫记》想起的
现在的人上了年纪,一是爱怀旧,二是爱出游。
马沙一不小心,小小年纪就滑到了新疆。新疆真是个好地方,马沙有口福,尝尽了沙漠中的仙果,想那王母娘娘的蟠桃,定然不及土鲁番的哈蜜瓜和葡萄。
除了品尝新疆的风味水果、饱览歌舞风采外,湖南人到新疆还有一个特殊的情结,那就是马沙是否见到当年王震将军召唤进疆的八千湘女?这八千个湘妹子是为北国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的啊。从花样年华到明日黄花,再到古稀之年,她们的悠悠岁月留在了祖国的边疆。进疆时,那里的环境真象唐诗人岑参的《走马川行奉送封大夫出师西征》一样“君不见走马川、雪海边,平沙莽莽黄入天。轮台九月风夜吼,一川碎石大如斗,随风满地石乱走”。在那样艰苦的条件下,巾帼不让须眉,八千湘女成了湖南人的骄傲。新疆建设兵团的各个团场都有她们的身影,她们也象西北的白杨树,刚劲、挺拔,不惧严寒,不怕磨难,经受了几十年的风风雨雨,不少成了当地的栋梁之材。还是那句老话,“唯楚有材,于斯为盛”。作为女知青的我,对她们很有一种崇敬的心情,如果能到新疆,定会寻访到那团场的一隅,会一会她们。长沙湘江风光带的北边屹立着一块巨石,据说就是从新疆运来的,那石头上铭刻着八千湘女的情怀。她们的婚姻、家庭,她们的悲欢离合,有兴趣的话,可以构思为现代版的《石头记》。前不久,湖南电视台终于寻访到几位当年的湘女,她们已是秋霜满头,精神却是格外的饱满。回到湖南拉起家常来还是一口难改的乡音,好熟悉啊!很难想象这是阔别三湘四水半个世纪的湘妹子。
马沙当年年少,斗胆单骑进疆,搭乘货车游南北天山,月黑风高夜宿兵站。异乡客可不是这样了,现代化的交通工具犹如孙行者一个筋斗十万八千里,早辞北帝、暮到江陵,倾刻间便到了拉萨。他借来阿拉伯飞毯,把西藏游的收获满打满地驮回到美国的家中。你看,寺庙挑檐上的铜铃,教徒们精典的长跪,尼洋河湍急的河水,米拉山口的油菜花香,在他的作品中都得到了充分的体现。看到异乡客镜头下的布达拉宫,我也感受到执着的教徒们从各地赶往拉萨,怀着万分的虔诚,一步一长跪进藏的悲壮和凄凉。经历了九九八十一难,而最后到达大昭寺时,他们的目的达到了,一部分人却因此而付出了生命的代价,真正到达了理想的天堂。
在异乡客的视野中,西藏既古老又不乏现代气息;既神秘又豁然开朗。西藏同胞勇敢和清澈见底的性格就是在这种环境中形成的。让我们走近韩红。她的歌声常在通往西藏的天路上与游客相伴,《天路》就是一首藏胞心底的歌。她出身在青藏高原,有着藏胞行侠仗义的性格。那年她开车在通往拉萨的天路上,途经一个上坡,前面一女司机开不上去,急得满头大汗,后面一位男司机一个劲地按喇叭,口里还大声嚷嚷。韩红下车帮女司机将车开了上去后,回过头径直走到那按喇叭的男司机前,挥臂就是一拳,“我是韩红!”说罢开车扬长而去。好像是打得不应该,但仔细想想,竟也有许多可圈可点之处。一曲《太阳岛上》让无数游人倾情于哈尔滨之夏,哈尔滨因此声名大振。一曲《天路》也让游人憧憬起西藏,铁路一通,游人就如织了。
异乡客此刻也许在努力地工作(此时正好是美国的白昼),经西行这一漫记,他又平添了许多收获,于是他把这些情感交给知青朋友,大家一起来分享。事情就是这么有趣,当你在读一篇陌生人的西藏游记之类时,你的思绪是很难先入为主地次第展开;而当你读到《我的西行漫记》时,你首先就会想到这是在异国他乡的知青朋友神游祖国后的感触,无限的乡愁在有限的旅途中得到了释放,因而你就会逐字逐句地去仔细品味其中的情趣。异乡客将拉萨的风土人情、高原美景象梳头发一样仔细地梳了一遍。他是那样地认真,生怕遗漏了什么,拉萨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都如数家珍,拉萨的蓝天和大地都尽收囊中,即便是上了年纪的老拉萨也不过如此。
马沙和异乡客奉献给了大家几顿精神大餐,在炎热的夏天读一读他们的游记会有一种清凉的感觉。就象当年英国人等待柯南道尔的侦探小说问世一样,大家每晚都端坐在电脑旁,恭候二位的新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