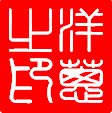我受一位靖县知青朋友之托为她写三个小故事。这可是她当年亲身经历过的……
(一)深山遇虎
我是1965年11月从长沙下放到靖县来当知识青年的,一行四男十三女被放在非常偏僻的铺口公社林源大队的大洞生产队。林源大队的生产队基本上是集中在靖县到新厂的公路23公里里程碑的马路两旁。
再继续往西北,马路沿着一座巨大岩石山的底脚,从阴沉沉的人工开凿的山底下穿过,就到一个看似无路却有路的叫“至上”的狭隘山口,那边就是藕团公社了。
大洞生产队却是在远离林源大队的地方。去我们的队是在23公里里程碑处下了马路往北走,一路上都是弯弯曲曲的羊肠小道。山路随着山坡的起伏越来越不好走,山坡两旁都是茂密而高大的参天古树,路旁的丝茅草有一人多高,经过时要不停的分开头顶上的茅草。有些地方就是大白天都没有得到阳光的普照,湿漉漉的路旁长满了绿色的苔藓和蕨类植物;一阵呼啸的山风吹了过去,哗啦啦!那排山倒海的松涛声让人听了都心惊胆战不寒而栗!
尤其是走到长有一棵白眼洋梅树的地方,那里叫“高阴”。阴森森的,更为吓人!那里是去大洞的最高点,也是唯一的通道;时常有凶猛野兽出没,据说这里还是当年土匪打劫客商后“关羊”的地方。
沿着湿漉漉的岩板小路往下走大约两里路就到了山底,这时候才能看见明亮的阳光透过树枝和树叶洒了下来,眼前豁然开朗,那里是一条长长的东西走向的大峡谷,峡谷两旁是长有茂密森林的层层高山,大大的田坝呈现在面前;穿过田坝的田径顺着一条弯弯的小溪往上走三里路就会看见有几个窝棚搭在那里,这里就是大队的新建队——大洞生产队到了。
几户社员是轮流进来在这里配合知青种田的,暂时都住在那临时搭建的窝棚里。山谷里不时传来一阵阵鸟的清脆叫声,不知名的野花香味也随风飘荡;算了算刚才走过的路大约有八里多,那艰难的翻山越岭和吓人的崎岖羊肠小道就有五里多……
我们十七位长沙知青的到来给寂静的大洞生产队带来了生气和欢乐。白天和社员一起劳动,晚上和社员一起欢歌笑语;入睡后往往也会被那野兽的吼叫声时常吓得惊醒,然后心惊胆战地久久不能入睡。
社员说:“这里经常有野羊,麂子,野猪,老虎的出没,还有红毛野人哦。”
这样的日子一直持续到1968年!
随着知青的招工和知青的大转点!这时十七个长沙知青只剩下了我和李裕慈二人啦。寂静的大洞又恢复了往日的宁静,我和李裕慈二人相依为命,艰难度日。苦苦地盼望有那么一天的到来,等待着能够离开大洞这人迹罕至的地方……
1972年的6月30日铺口公社为了迎接7.1党的生日,举行了各大队的文娱会演。
能歌善舞的我是林源大队的文娱骨干,这时我们大队的知青也寥寥无几了。当天中午和我相依为命的知青李裕慈把我送到了上山的路边对我说:
“快去快回哦,我一个人留在家里我好怕的!”
“好,放心!我会很快就赶回来的。”我一口就答应了她。
她性格内向,由于家庭出身不好成分蛮高,尽管她各方面表现都很好但是和我一样,招工和读书都与我们无缘。在这些个日子里她主内,我主外!就象是一个模范小家庭那样过日子。
我和大队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的年轻男女社员们走路来到了公社,各大队的演出人马都已经云集在那里了。我帮我们大队的演出人员化好装以后,马上上台表演了:风靡一时的反映军民鱼水情的“洗衣舞”。演完后台下报以一片热烈的掌声!最后宣布:我们大队的节目出乎意料地获得了第一名。
汇报演出完毕,天色渐渐黑了。大家趁着夜色沿着蜿蜒的看起来白白的公路兴高采烈地往回家的路上赶;忙碌了半天的劳累都抛之九霄云外,一路上大家都沉浸在刚才获得演出成功的喜悦和无比的高兴当中。
走到林源大队时天色已经很晚很晚了。天墨黑墨黑的伸手不见五指,我根本不可能回到我的大洞生产队了;我只好住在本大队下寨生产队的结拜姐妹见梅的家里,等明天一黑早早点起来赶紧赶回我的家——大洞。
回大洞心切,我迷迷糊糊也不知道睡了几个小时就醒来了。天还是黑黑的,我心想:反正睡不着了,走吧。
见梅和德茂夫妇还在隔壁房里呼呼地打鼾,我手里拿了在公社向陆秘书要的一卷旧报纸蹑手蹑脚的摸出了堂屋,顺手轻轻的带关了他们家的大门。
刚跨出大门眼前迎来了一片黑暗。我站了一会儿,啊,还好,清楚了!没有月亮的天空,满天的星星在眨着小眼睛;路面还是依稀看得见是白白的;凉爽的山风一阵阵吹来好清新的空气;喔喔喔,鸡也开始叫啦!
我急匆匆的走出了寨子又上了马路,在23公里里程碑处摸下了马路,朝着模糊不清的小路缓缓的往北走。山风一阵紧似一阵,发出呼呼的叫声,我一脚高来一脚低的在凹凸不平的小路上往前赶;心里想的是快点到大洞,李玉慈她要望眼欲穿啦!
有些地方要分开头顶上丝茅草,弯着腰钻过去。有些地方就是大白天都没有多少阳光照进去的地方还是墨黑墨黑的,只能睁大着眼睛凭着感觉走。湿漉漉的长满了苔藓和蕨类植物路上也能走出啪啪啪水的声音来。
天空慢慢地泛出了鱼肚白,天边也能看见一些云彩。
我开始大声地唱起歌来了。“你看那高山顶呃,白云间……”我大声地唱起那歌剧“江姐”里的歌曲。
拿在手里的那卷旧报纸我作为指挥棒一样左右来回有力的挥舞着,脚步一点都没有放慢;头上也开始冒出了热气,我感到衣服渐渐的有些被汗浸湿了。
东方的朝霞出现了,太阳快出来了。山谷里传来了一声声鸟儿的清脆叫声,这不就是那棵白眼洋梅树吗?哦,是的。我已经到了去大洞路上的最高处“高阴”啦。
忽然,哗啦啦!一阵呼啸的山风吹了过去,那排山倒海的松涛声让我心中一惊。远远的望过去在那当年土匪打劫客商后“关羊”的地方的草丛中隐隐约约躺着一只黄色的东西看不太清楚。
我们大洞的牛是经常在晚上打脱牛栏的栓子跑到外面的山坡上过夜,害得我们第二天又要满山遍野的找牛。
呃,那只怕是头昨天晚上跑出来的黄牛吧?我心里随便想了想……
我没有停下劳累的脚步,漫不经心地走到了离这头“黄牛”差不多四五米远的时候,那头“黄牛”慢慢地懒洋洋的爬了起来啦!
啊,这哪里是什么“黄牛”噢,我浑身一麻!那是一只黄色和黑色花纹相间的斑烂大虎!老虎走了一两步后在长长的舒展自己的身子,四肢趴开伸了一个大大的懒腰。
那一瞬间我停顿了,我张开了大大的嘴巴不知所措!我清清楚楚地看见,老虎有我房里的书桌那么大!那卷旧报纸被我捏在手里一动也不动啦,我脑海里一片空白,而脚步还是在机械似的不停地走啊走。
我根本就不知道跑,也不敢跑,只知道一门心思地本能的往家的方向提着脚步。当我走到了湿漉漉的岩板小路旁边的一棵大枞树旁,那只老虎也不知道在什么时候斜斜的走到了和我平行的高堪上啦!它在高处我在低处,那棵大枞树后面也是个高堪子。我惊呆了!我停住了脚步,目瞪口呆的望着那高堪上的老虎,我双腿僵硬而感觉到在发抖,我斜斜的靠在那棵大枞树上,指挥棒似的那卷旧报纸已经不知什么时候掉到了地上,时间一分一秒好象已经凝固了。
忽然,那老虎对着我大吼了震耳欲聋的三声,“刷!”地,那老虎从我的头顶上一罩而过!我软软的滑到了地上。那叫声迎着刚刮过来的一阵山风,简直象地动山摇!树叶儿都刷刷刷的掉了一地……
我靠在那棵大枞树旁一动也没动,什么都没有想,麻木啦……
当我惊魂未定,一切的一切又恢复了往常的平静,好象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
“哎呀!我还在,我没有事,我命大!”我心里在喃喃地自言自语。
我咬了咬牙,从地上振作地爬了起来。不管三七二十一的拖着疲惫的身子慢吞吞地走到了山底。
这时太阳已经出来了,明亮的阳光撒满了大地。山谷里又传出了一阵阵鸟儿清脆锐耳的叫声。我看见了宽宽田坝,看见了弯弯的小溪,看见了我们大洞出早工的社员模糊的面孔,也渐渐看见了李裕慈……
“呃,刚才饶永良一定遇见了老虎!”社员们都在说。
他们刚才都听见了山中老虎的那三声吼叫声!
我被大家迎进了屋子里,大家好心地围着我,拍打着我的背心。
我呆呆地坐着坐着,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大约过了二个小以后我才慢慢地恢复,才开口说话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