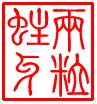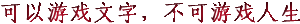这是本人于1976年写下的一篇军旅生活有感小文,谨以此文纪念建军八十周年!
战士心中的母亲
离家好些个年头了,而母亲的形象无时不在心头。
记得最初离开母亲的时候,我才十六岁,跟着一帮同时走出校门的同学少年,到了湘赣边区罗霄山脉一个叫做大洞岭的山里当了知青。两年以后,我在知青点报名参军远赴边陲,从此,和母亲的距离逐渐遥远。
刚刚离开母亲的时候,凭着一股只想天高任鸟飞的念头,面对泪眼婆娑送别的母亲,少年懵懂的我并不懂得什么叫离愁别绪。下乡三个月后,我第一次获得探家的机会。事先我并没有告诉母亲,可母亲却不知从哪里得到信息,竟独自走到车站去接我,我在车里猛然瞅见母亲已然有些老花的眼睛在人群中焦灼地搜寻我,那目光,使车上的我突然感到某种震撼,从此,那目光便一直尾随着我,从罗霄山脉的大洞岭到腾格里沙漠的军营。
如今展示我新生活的地方,是祖国的西北边陲。穹隆之下,但见沙浪千里,三三两两的骆驼草,点缀着这片缺乏生机的国土。曾经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春来江水绿如蓝”的浏阳河和湘江啊,和母亲一起,竟然变成遥远的梦境,不可望,更不可及。乡思,在苍凉的边关战士心头油然地升起。而此刻,这种乡思竟是如此地浓烈,甚而,竟能使我散漫于自己作为一个军人的职责。
记得那是当新兵时仲春的一个夜晚,正是沙漠四月的风季。江南温馨的月来到这里,在呼啸的风沙中放射着朦胧而苍凉的光。我和老班长一人挎着一支冲锋枪去巡逻。好不容易挨到快换岗的时候,天空突然黄云骤起,吞星盖月,肆虐的风沙如狮子般吼叫着奔突于天地之间,打得人趔趔趄趄。我和老班长不得不在一个牧人留下的用土坯砌成的废弃羊圈稍事躲避。一边盼望着轮值的战友快来接班。这时,老班长突然拍着我的肩膀说:“快看,那是什么”?我顺着班长的指示往远处瞄了一眼。只见羊圈外面的大漠飞砂走石,有一团东西随着沙石一起时而落下时而飞动。我说:“稀罕啥,不过是一块土坷拉罢了。”老班长说:“指导员说了,北边的熊瞎子一直对咱们虎视耽耽,可不能麻痹大意”。我不无调侃地说:“这么个破地方,谁稀罕!”“你说什么?破地方?”老班长显然对我的说法生气了。可他很快就克制了自己,不由分说地拽着我的肩膀,顶着风沙强大的推力,追到了那个可疑物。仔细一看,怪了,竟是一包敌方的宣传品。看样子,它早就被遗落在大漠边陲的某个角落,如今被这大风搅起,正巧被我们发现了。我顿时为自己差点亵渎军人的职责感到自责,同时对老班长的警惕性暗生敬意。
第二天傍晚,老班长和我肩并肩,沿着沙枣花香的沙漠小路徐徐地散步。我知道,班长是要为我所谓“破地方”的说法批评我呢。出乎意料,班长却问我:“你爱自己的母亲吗?”我说:“那还用问吗?”班长说:“我给你讲一个母亲的故事吧。”
班长说:“很久很久以前,有一位勤劳美丽的母亲,她生养了许多的孩子,她练取了五彩的云霞为孩子们做成天空,她从五荒山运来泥土做成大地,她化仙界的种子为庄稼,把乳汁集成江河,让孩子们免于饥渴。可是后来,一些妖魔嫉妒母亲家园的富饶美丽,疯狂掠夺母亲的财富,甚至企图宰割母亲的身体。。。。。。”
虽然是自小就学过的民间故事,经老班长说出却让我生出新的领悟。可我还是说:“班长,别把我当小孩,这是中国上古神话女娲的故事,谁不知道啊!”班长说:“我看你就不知道,你只爱你个人的母亲,却不爱祖国母亲。西部边陲是祖国母亲的一部分,作为祖国母亲的儿子,作为一名军人,怎能对母亲的安危掉以轻心?”
班长一番浅显的道理,却实实地深入了我的心。按说,我看的书实在不比班长少。记得我最为喜欢的西部维族诗人木塔里普的诗歌中,就有这么一段警句:“先作祖国的儿子,后作母亲的儿子,最崇高的爱情是爱祖国!”可是我的思想境界却不如班长,因为我忽略了一名军人应该懂得的这么一个简单的道理。
自从和班长一起散步的那个夜晚之后,腾格里——大漠——祖国——母亲,几个单词逐渐糅合到我情感的深处,她是那么厚重。而辽阔的大漠、起伏的沙海、坚强的红柳、甚至那弱小的沙枣、甚至那更为弱小的骆驼草,都在悠悠的军旅岁月中逐渐变得美丽。因为我心中有了一位更为伟大的母亲——那是战士心中的母亲。
此后,我并没有减弱对母亲的思念,相反,心中关于母亲的内涵更为深厚。我少年粗糙的心因此而逐渐变得细致,以致能用这种细致去体察风声鹤泣中的异常;而我脆弱的意志也逐渐变得坚强。哪怕在营建施工中钢筋穿透我的脚背,哪怕在对抗训练中手中灼热的机枪烧红我的胸膛,哪怕在自卫反击战中面临生死的考验,我依然没有放弃一名战士、一个儿子的责任。
我在一个儿子对母亲应有的爱与责任的领悟中成长,逐渐由一名懵懂少年,成为共和国一名职业的守卫者。
(80个知青娃于公元1976年写于西部军营,修改于2007年建军节前夕。题图为我和先我提干的班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