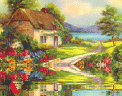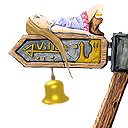在王百明去世一周年的日子里
.陈乃广.
公元一九六八年八月,盛夏的炎热伴随着文革后期仍保留在人们心中的狂热,犹如乌云一般笼罩着湘南大地,使人感到喘不过气来。
知青们大多被从长沙遣回到了江永,农艺队的当然也不例外,大家都陆续从长沙回到队上。八月中旬的那些天,农艺队的气氛显得格外沉闷,王百明逝世一周年了,大家怀念着他,心情都很沉重。百明是农艺队的一名长沙知青,去年的八月十七日在江永县城无辜被江永农民枪杀,为给凶手开脱罪名,县里竟有人硬把他说成是反革命!
八月十六日那天,我到县城挑粪回来,告诉大家在县城看到满街都在张贴标语,为把王百明打成反革命大造舆论,大家听后心中更是悲愤交加,难以平静。
下午,我们十几位队员集中在小会议室里,秘密召开王百明追悼会。会场布置很简陋,正面挂着王百明的一张炭笔画像,那是几天前我根据百明学生证上的小照片放大的,镜框原来框着一幅水彩画,画像就藏在水彩画的后面,今天拿掉了水彩画,露出了百明那瘦晰的面庞,遗像下悬挂着一朵白纸花,显得分外孤独和凄凉。 没有哀乐,没有花圈,队长郑华用他那深沉的男低音宣布:“全体起立,向我们的好战友王百明烈士三鞠躬,默哀三分钟……” ,会场安静极了,只有窗外的知了在哀声鸣叫,有几位女生呜咽起来,声音越来越大,后来会场里竟引发了一片痛哭声,这种发自内心的悲苍是为含冤死去的好战友,也是为了前途渺茫的自己,三年前张开双臂欢迎我们知青的这片土地,怎么突然的就变成吮吸知青鲜血的战场?
透过蒙蒙的泪水,我似乎看到长着一头卷发,个头不高而神采奕奕的百明兄……。
在农艺队创业的日子里,我们同住一间茅草棚,晚上,寒风从屋顶灌进来,一次又一次吹灭了煤油灯,百明倦缩在帐子里,用左手着盖着灯罩口,右手不停的写作,他非常热爱文学,心中有着美好的理想和追求。 我一觉醒来,已是深夜两点多了,他还在看书,有时饿了,就用晚饭时留下的二两白米饭来支撑自己疲惫的身躯。白天田间劳动很繁重,百明总是埋头拼命干活,工间休息时,他一头倒在田埂上便可酣然入睡…… 。 而现在,他那二十二载美好年华,伴随他的理想和抱负,长眠在都庞岭下,融化到潇江水中。 逝去的他怎么也不会明白,活着的我们也实在想不通,一个热爱生活、有着美好追求的青年人怎么就会变成了反革命?
“不能让他们污蔑百明的冤魂!” 一个革命行动的想法油然而生。散会后,我们各自拿出纸和笔,写起了小标语。“王百明为革命而死,重于泰山!”“唯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不多时就凑齐了一百多张,大家商定半夜就开始革命行动。
十七日凌晨两点多钟,大家都起床了,大姐煮了一桶浆糊,队员们分成五组,向县城出发。没有月光,也没有风,八月的夏夜十分闷热,加上心头兴奋又紧张,很快就感觉汗流浃背,从农艺队到县城七里路似乎走了很久很久,终于看到了黑压压的山影下有一片稀落的灯光,那便是江永县城了。
大家分散插小路进入城内,江永县唯一的一条大街上空无一人,一条用石灰水写在地上的硕大的标语,在惨淡的路灯下格外刺眼:“谁为反革命分子王百明翻案,就砸烂谁的狗头!”抬头一看,街道两边墙上都刷满了打倒王百明的横幅,落款全是县城各造反派组织, 今天将是县城赶场,进城的人会很多,难怪他们昨天忙乎了一天,他们真是要在死人身上踏上一只脚,让他永世不得翻身啊! 热血在我们的血管中膨胀! 我们三人一组用饭钵盛上浆糊,分散到街头巷尾,把我们写的标语张贴起来。半夜的脚步声引起街道两边住家院内的狗阵阵狂吠,我们紧张的靠着墙边移动着,如同当年地下工作者出生入死一样,大家将标语覆盖在对方的横幅上,贴在各商店、机关、住家、长途汽车上,我和胡干子甚至从县革命委员会食堂门上的小窗口爬进去,将标语贴在了食堂的菜牌上!
东方开始发白的时候,我们已离开了县城,忙乎了一宿,竟然毫无倦意,回到队上稍事休息,上午十点多钟,大家又装着赶闹子的样子来到县城看热闹。 看到人们三五成群地围着我们的小标语议论;看到各地来赶闹子的知青们脸上那掩饰不住的喜悦与惊讶,我咽下苦涩的泪水,心头掠过一丝甘甜。
三十八年过去了,好多事情已渐渐淡忘,然而那惊心动魄的一夜,却永远记忆犹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