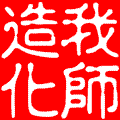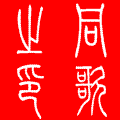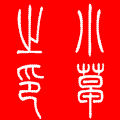论项羽“不肯过江东”的虚构
《项羽本纪》是《史记》传记中最为精彩的一篇。项羽是司马迁着墨最多的一个人物,在他身上倾注了作者强烈的惋惜和同情。垓下一站,项羽乌江自刎,尤其写得气势磅礴,跌宕起伏,成为中国文学史上的一篇不朽佳作,早已家喻户晓,历代传诵。
当项羽逃奔至乌江边,遇乌江亭长驾船在江边守候,欲渡项羽过江,而项羽拒绝,最终只将坐骑送走。本文认为这一段描写应为作者的虚构,不是历史事实。其主要理由如下:
一、没有旁证
项羽与乌江亭长的对话,纯为两人之间行为,并无第三者在场作为旁证。项羽旋即战死。唯一知道这段话的只有乌江亭长一人。司马迁何从知道他们二人之间的对话?全凭乌江亭长一人所说,其可信度值得怀疑。另有二十六骑在项羽旁边,但两人对话时,据书中描写,似乎未参与旁听。退一万步说,即便参与旁听,此二十六骑也必然与项羽一道战死,不可能一人留存。
二、乌江亭长是否确有其人
作为如此重大事件中的重要人物,作为唯一能将二人之间的对话流传于世的人物,姓氏名讳不交代,何方人氏也不交代,以及后来的行踪不交代,这是说不过去的。韩愈在《张中丞传后叙》中提到听某人说到某件事,对“某人”姓甚名谁,何方人氏,以及原来在何处,后来迁到了何处,他的后辈又到了何处,有何遭遇,交代得一清二楚。目的无非是以此说明所言不虚,并非道听途说。应该说乌江亭长更象虚拟的人物。
三、情节过于巧合
垓下战场在今安徽省亳县,乌江镇位于今安徽省和县,两地相距一百余里。“乌江亭长檥船待”,既然是“待”,乌江亭长显然是预计项羽必然在此渡河而守候。但在当时的条件下,乌江亭长何以能遥知远在一百余里外的战事进展状况,何以能预知项羽一定会失败,一定会突围,一定会沿这条路逃往这个方向,一定会在这个时候,到达他所守候的地点?这种过于巧合的情节一般只会出现于小说、传奇和戏剧中,现实中出现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四、乌江亭长的行为不合常情
项羽为人残暴凌虐,未见有何德政,其统治并不得人心,人民对项羽的失败并不同情。“项羽至阴陵(今安徽定远县),迷失道,问医田父,田父给曰……”当项羽逃跑途中向农夫问路时,农夫有意欺骗他,便是明证。乌江亭长个人的命运与项羽应该没有紧密地联系。他可能有一定的倾向,但决不至于冒灭族之祸来特意地、决非一时冲动
地“待”项羽渡河。况且项羽之败,决非偶然。其为人思维方式简单,刚愎自用,并无统御之才。当他居于绝对优势时,尚且不能取胜。今只剩孤家寡人,纵使渡过乌江,卷土重来,结果也是一样,顶多是延长战争时间。乌江亭长应该是看到这一点。一边是灭族之祸,一边是取胜的可能性及其微小,作这种不相称的赌博,不合人之常情。唐代杜牧有诗句“江东子弟多才俊,卷土重来未可知”,虽然代表了部分后世读者的心声,但毕竟感情的流露多,而理性的分析少。王安石到了乌江亭,见到杜牧的题诗,于是也题诗一首:“百战疲劳壮士哀,中原一战势难回。江东子弟今虽在,肯与君王卷土来?”在他看来,江东子弟纵然多才俊,恐怕没有人愿意再干了。
五、项羽不渡江不合情理
项羽在垓下被围,趁夜色率八百余人突围,过淮河后还剩一百余人,至东城(今安徽定远县),剩二十八骑。始终不能摆脱汉军的追击。为摆脱追兵,又率二十八骑返身杀入汉军,再聚时,剩下二十六骑。项羽一路奔逃,返身杀敌,其目的只有一个,便是摆脱追兵,逃得性命,以求卷土重来。可是好不容易跑到了乌江边,正好遇上了一艘愿渡他过河的小船,他却又不渡江了。这显然不合情理。他如果自认为无面目见江东父老,何必从垓下突围,一路奔逃。存心要战死,在垓下即可,在东城亦可,何必跑到乌江边来。
六、未见当时人提及此情节
项羽逃到乌江边,遇乌江亭长欲渡他过江而不渡,如果确有其事,在当时应该是流传于世,而为人知晓。如此重大的,富有戏剧性的情节,一定会有当时人提到。然而翻遍所有史料,未见有当时的任何人有任何只言片语提到此事。尤其是韩信,作为当时汉军的主帅,无论如何应该是知道这一情节,并且一定有所感而发,然而没有。《史记》中通过他的口,对项羽的形象做了生动的塑造。然而对如此重大的情节却没有提及,岂不怪哉。《汉书》、《汉纪》基本照搬《史记》,因而不可作为佐证。
综上所述,《史记·项羽本纪》所记之垓下之战,项羽“不肯过江东”的一段文字,应为作者司马迁的虚构,属于文学描写手法,也有可能为当时民间传说,司马迁未予确证而内心十分愿意认可,用他那枝生花妙笔,写成一段千古绝唱。但真实的历史事实应该是,项羽逃到乌江边,无法渡江,追兵蜂拥而至,不得已自刎而死。
那么,司马迁为何要作这种虚构呢?
众所周知,司马迁因李陵一案而受到牵连,遭受了仅次于死刑的宫刑。这对他是极大的耻辱,这种内心的极大的痛苦,在《报任安书》中说的很明白:“故祸莫憯于欲利,悲莫痛于伤心,行莫丑于辱先,而诟莫大于宫刑。”这种奇耻大辱,在司马迁的心中,终于转化为一种复仇的心理。这种复仇是通过《史记》的著述来完成的。在司马迁的笔下,汉家统治者受到贬损,如写刘邦的虚伪、狡诈、残酷。《项羽本纪》中记载,刘邦被项羽追赶,他为了尽快逃命,不惜将自己的亲生女儿孝惠、鲁元推到车下,还是滕公几次下车将两个孩子抱回车上。项羽以烹刘太公要挟刘邦,刘邦说:“吾翁即若翁,必欲烹若翁,则幸分我一杯羹。”活脱脱一个无赖。诸如此类的记述不胜枚举。又如《封禅书》记载汉武帝求神君仙人,尊骗子
他往往从失败者身上看到自己的悲剧身影,因而为这些人物作传时融入了自己的感情。如《屈原贾生列传》。李晚芳《读史管见·屈原列传》:“司马迁作《屈原贾生传》,是自抒其一肚皮愤懑牢骚之气,满纸皆俱是怨辞。”
司马迁在对汉高祖刘邦的明讽暗刺的同时,对项羽的描写却是充满了深切的同情与热情地歌颂,集中了许多重要事件突出他的喑恶叱咤,气盖一世的性格特征。《项羽本纪》通篇文章情节起伏,场面壮阔。其中给人印象最深的仍是垓下之战。
司马迁显然是为了可以完善项羽这一英雄人物的形象,不惜对项羽生命的最后一刻,做出了大胆的虚构。人固有一死,或者壮烈,或者平凡。显然在司马迁看来,像项羽这样的顶天立地的英雄,他的死不应该太平凡。于是他为项羽的死做了这样一种虚构。他认为这种行为方式符合项羽的性格,也符合他的身份。
虚构在《史记》中大量存在。这种虚构不同我们今天的“戏说”。在不违反与改变历史真实的前提下,司马迁对某些细节的描写,明显采用了虚构的手法,以期情节更为生动,人物形象更为丰满。《史记·高祖本纪》记载,韩信平齐后,派使者到刘邦那里,请求汉王刘邦立他为“假(代理)齐王”。“汉王大怒,骂曰:`吾困于此,旦暮望若来佑我,乃欲自立为王!'张良、陈平蹑汉王足,因附耳语曰:`汉方不利,宁能禁信之王乎!不如因而立,善遇之,使自为守。不然,变生。'汉王亦悟,因复骂曰:`大丈夫定诸侯,即为真王耳,何以假为?'乃谴张良往,立信为王,征其兵击楚。”在这段记述里,张良、陈平“蹑汉王足”和“附耳”低语,显然无人所见,无人所闻,而刘邦态度的转变,也无人所见,无人所闻,可以断定为司马迁的虚构。有了这种虚构,情节顿时生动,人物性格顿时栩栩如生。读者如眼见其人,耳闻其声,有身临其境之感。《史记》是史学著作又是文学著作,所谓“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虚构功不可没。
文章的最后,我们不得不提到李清照的诗:“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生逢乱世,国破家亡。李清照在急切地呼唤一个像项羽这样的英雄,呼唤着一种视死如归、勇往直前的精神。但是我们认为这种呼唤并不意味着对历史记述的确认。就象我们提倡愚公移山的精神,并不等于认为确有愚公其人其事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