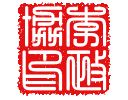设计在我心中的知青雕塑
看到知青网关于知青雕塑的议论,我很自然地在心中设计起一座知青雕塑。我把雕塑取名为“仰望苍天”。
我以为知青可以说是“思考的一代”人。
1968年底老三届学生下放农村转变成知青身份,应该是他们思想转折点。当时,对于“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大多数知青的认识是盲目的无奈的。既然“最高指示”都要去,还有什么可说的?假如你成分不好就更不要说了。出身红的和黑的黄的都去,你去我去他也去,也许还有了一种平等的快感。特别是处在十六岁花季(用这个词真有点奢侈)的知青,早就厌弃了令人窒息的学校,沉闷的家庭,向往独立生活的新天地。他们哪知政治的险恶,哪懂苦难是回什么事。你去我去他也去,去了,也许还有过一窝蜂的快感。“到农村去,到祖国最需要我们的地方去。”这一去,有人就一脚深深踏进了无尽的苦难。这一去,众多知青就陷进了生活的艰难竭蹶之中。这一去,除了个别知青,最后的选择只能是“胜利大逃亡”。因此,知青落脚到乡村的土地之后才开始独立思考并拷问自己,才在政治上真正成熟起来。在广阔天地他们才不约而同地脚踏黄土,仰望苍天,上下求索。知青一代和上下几代最大的不同是,他们对国家对民生有过更多更切身的思考和体验。知青确确实实称得上是“思考的一代”人。
设计在我心中的知青雕塑是截取知青生活的一个断面:三位知青。一男一女正拿着锄头和箢箕准备出工;另一位知青提着背包即将离去,是病退回城是转点是招工是升学?这是一个让人伤感,令人心悸的瞬间。
男知青眼镜后的眉头紧锁,眼睛迷茫地仰望苍天,磨破的衬衣露出结实健康的肌体,提着箢箕,握着扁担。他可能正是朱学勤寻找过的“68年人”——“思想史上的失踪者”——有理想有追求的人。
女知青扎着羊尾辫,眼神充满企盼地回望蓝天,嘴唇紧闭,一手扶着锄头,一手将家信塞进口袋。她可能正是王小波所说的“沉默的大多数”之一。
另一位知青眼睛平实地望着前方,这是一双看破世事,回归世俗的眼睛。疲惫的双肩低垂,双手无力地提着背包。他历经坎坷曲折终于能够离开这块黄土,却没有一丝喜悦。他将回到68年的出发点。他不再是他。他就是今天的你,今天的我,今天的他。
这座比真人高不了多少的圆雕,没有方向,没有单独的底座。精雕细刻主要集中在三个知青的脸部;中部依石而凿出每个知青都抚摸过的箢箕扁担锄头和背包;下部概括处理,与底座融为一体,偶见从破旧解放鞋中突破的脚趾。三人背靠着背,几分迷茫,几分企盼,几分无奈,在问天!
知青的本质是低调的,他们大多数人都没有什么值得炫耀的本钱。所以造型不应该是外在的飞扬,而应该用雕刻把他们“心灵的活动”固定下来,表现知青在求索中含蓄的激烈的内心冲突。这种冲突一直在每个知青的心中不能平静,并延绵到今天。由于对苦难的理解角度不同,感受不同,今天他们还会为“青春悔不悔”而苦苦争辩。这种思想的探求,并没有因为过知天命之年而衰减,反而来得更加强烈。大家对知青雕塑如此感兴趣便是最好的佐证。
当我看到征集知青雕塑方案的文章时,我对建知青雕塑知青浮雕的影墙和知青广场隐约有一种担心,很怕知青中隐秘不为人察觉的虚荣吞食了当年下乡的真实感。我们千万不要用标语式的审美观念建一座雕塑来简单诠释知青这个名词。由此,我不认同文斗先生那张草图里造形的设计思路:一人挺立,两人弓步前倾,提着盏指路的灯。这种完美舞蹈式的造型是68年前的学生,而不是68年后的知青。
我缺乏雕塑技能,我说的都是心中的知青雕塑,因此也只是说说而已。(2007.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