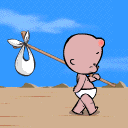是非与利弊
草原野狼 / 文
是非与利弊,是人生的两个座标轴,而它们的座标交点,便成了一个人的价值。
有人可以不管是非,可以看轻是非;只要能追求到的利益,他便做到可脸不变色心不跳,而断然抛开与远离于他不利之任何顾虑牵挂。
有人却又太计是非,是非为重;因此,常常人生一场,鲜血横流,伤痕遍体,甚至,很早放弃生命。
大多数人,则是处于有些是非观,却又也不忘利弊的警觉之间。
大多数人之间的区别,便只是他究竟属是非情感占多一些,还是利弊考虑为重一些?
几个人相交,共事,一般来讲,我们通常看到的是,凡属是非、情感较重一点的人,他吃亏的状况就会多一些,而对利弊后果想得清楚的人,则往往要占些便宜。
有些事,并非人家脑子不明白不理智,但他之所以吃亏,实吃在是非与情感上。明明有些事会于他不利,但他在利害与是非之间,宁肯明明白白地选择吃亏,也不愿放弃是非的坚守,义气第一,利益押后。
然而,世间对人生的成败判定,往往却只以结局为准,并不甚计量动机的含金度。
是非之分,只是以后道德与历史评价的事,而所获得或所失去的利或弊,则会在当时即予显现。得利者即可弹冠举杯,受损者则要立马自饮苦酒。而且,世人却又常常只认成败,健忘那之中还有着的是非。何况,有些是非,本来就是局限、隐藏于那些成败之后,不为他人所知。
平津战役中,国民党天津守军司令陈长捷,其实他早就知道大势已去,不能与解放军打了,但由于他忠实于其长官傅作义,不想在傅之前就放下武器,而希望在傅之后再降,至少也要与傅长官同时起义。然而,傅却拿陈的忠心做了谈判筹码,明明他巳在与共产党莶和平条约了,却还命陈坚守不降。结果,傅做了起义将领仍居庙堂,陈沦为战犯却陷地狱。所以,当傅作义事后去战犯所看望陈长捷时,陈愤而拒见。此事,幸世人皆知,否则,陈长捷真太冤了!但,就是世人知道陈是讲义气的“是非”观者,又如何?谁能还给他作为战犯而被囚禁的十来年光阴!
陈长捷这类遭遇,想必处世之中,人们都多多少少、大大小小、形形色色而有过体验;陈长捷事后有过的愤闷,也许我们都也不同程度产生过。
人世间很多事,都令人深感不平,也生出些茫然:这是非观念,到底是要,还是不要?
对此困惑,曾国藩有一解法:“程朱之理为纲;申韩之法为用;黄老之道为心。”
程朱之理,讲的是道德,就是人生是非观,申韩之法说的则是利弊线,即为人生操作法。
是非观乃做人之本,故不能不讲,程朱之理仍应坚守,不讲是非者,枉为做人。
但却不能纯只守此,而还须用申韩之法、利弊观念适当制约,以免自己总是受伤不已,常为“冤大头”。乐于助人之善举,见义勇为之理念,确应常有,然援手之际,却也不应忘记自己可付出的底线,不忘得以自保的机灵,以免在舍己待人之后、体肤负伤之际,心中却要流血;哪怕就是施舍予街头乞讨者,也须定睛看清楚:那乞者是否确真有难?而并非是有人在利用乞者与你的同情心,骗窃你的钱财。否则,你不仅会枉失钱财,更会由此心灵受挫。
持程朱,行申韩,仍还不够 ,最后,还须用一心法平衡:黄老之道。
没有黄老处世哲学之心法,要做到是非与利弊的座标交叉,正为适度,则难于办到。因为,人心,毕竟不是一碗水,不是想放下就能放下,想端起而就端得起的。你的心智,也不一定次次清楚,观人察事,未必能件件无误,由此而上当受挫,自难避免。
黄老之道的精髓,就是一句话:几十年的人世游,要常常能想得开,不要与自己过不去!
人各有各的活法,既然不想丢弃过去有了的人生操守,“洗心革面”,而又也不想再经常受挫受伤,曾国藩说的这三件武器,似正适用。
2007/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