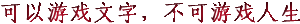师傅娘子
公元1972年的一个冬日。洞庭湖滨一乡镇的酒馆里。我和几个换命的知青兄弟杯觥交错。我爱大清国,大清国却不爱我。自1968年下放后,多少次的招工机会竟无缘置喙,凭任湖风冰凉心血,清浊唱广陵,涉江行天问,醉今朝,梦偷欢。
正到酣畅之处有人摇肩膀:“邓伢子,快回去填招工表”。
我被招工了。十几天后,一张单程船票送我别离沅江,终点站是一个小城。这仅仅是一个苍白的地理概念,不是我的故乡长沙。我没有“千里江陵一日还”的轻快,行囊里除了迷惘、颓废、悍野、磨难之外,还有思索的疲惫等,背负沉重。
小城的东端有几家织布厂。未及半年,我就这个厂那个厂调出调进转圈,终于在一家落下脚来,当锅炉工。
1.
莺飞草长四月天。织布厂的锅炉车间。一条通道经过此处通向澡堂。通道上煤渣堆积,胡乱撂着撬炉膛的钢钎。我等几个蹲在这里歇气,状似泥蛙,更像伸出舌头哈哈煽气的狗。
排骨老兄从炉膛边踱步出来,一手拖一钢钎,一手褪下手套;两指头抠搜着从裤兜里夹出铁皮烟盒,用嘴叼出一根纸烟,蹙到烧红的钢钎上吸燃了,啪地把钢钎一扔,猛劲吐出几口黑唾沫,像狗一样摇晃抖擞甩去赤脯上的汗珠瓣;再端出一个硕大的茶缸,大口咕嘟灌下酽茶,“妈妈B,是人搞出来的崽就不得当锅炉工。”
远处有铃朗笑语传来,打眼望去,一群女工打从织布车间奔涌而出。个个挎着提着装有洗澡换洗物什的铁皮桶子;一路行来,摘下白帽子褪去白兜兜,生动蜕现出五彩斑斓的花衬衣,灵动泼撒着瀑布般的黑发,恣意拍击着各色拖鞋噼里啪啦,形似一群欢快的梅花鹿。
走进了,一女子说话调软声嗲,“排骨老兄,今天是那位师傅招扶我们啰”。排骨老兄嘴叼的那根纸烟顿时有了邪性,先望那女子上下撩拨一番,再转悠着指向我,“我徒弟长沙满哥等的好性燥,只怕你不来过水清炖哩。”
再走近了,面对横亘着的堆堆煤渣,还有横七竖八佈下的钢钎阵,女工们踟蹰起来,就像鹿群穿过死亡沼泽,一个个小心翼翼寻隙觅缝插脚踮起过,嘴里还哎哟哎哟地惊叫。经过我们身边时躲躲闪闪,一幅怕被狗咬的样子,唯恐蹭上黑煤灰、粘上汗臭味。有似巫婆咒语细声传来:“该死的煤炭鬼子不做好事,一世找不到堂客的。”
走过去了就是澡堂。鹿群又撒起欢来,调笑打闹一哄而进,铁皮桶咣咣乱响。一婆娘往外高声放话:“满崽子放水啰,你屋里老娘要褪毛哒!”
我猛开热水笼头,里面惊恐声大作:“蠢宝崽哎,放点冷水啰!”
我关死热水,又猛开冷水笼头,里面放声怒骂:“你这个忤逆崽,想要冻死你屋里娘呗。”
我又关死冷水,猛开热水笼头,……。
有人一把推开我,三下两下把水调匀,这是排骨老兄,“郑姐,这不怪我……”话没说完就被打断,“不怪你怪哪个,你是师傅,他是徒弟。”这是女声,有着小城特有的味道,糯性足,此时不怒而威。
我回过头看这位郑姐,身材高挑,瓜子脸,眉弯柳,眼线细长。看样子是匆忙间冲出澡堂来的,头发湿漉漉的还在滴水,颈下的纽扣来不及扣好,犹隐还露的肌肤白皙一片。那妩媚眼神向我,审视、包容、嗔怜等什么意思都有。
“你看你一身好邋遢啰。”我光着上身打赤脯,胸脯上胳臂上脸上一道道煤黑印,头发粘满了煤灰。下身的那条厚布工装裤,煤灰汗水浸渍成垢起硬壳,脱下来可以矗立不倒。
“你是转了几个单位才到我们厂子里来的吧。”这是我到后来才明白的内情,原来这里的织布厂都是小作坊起家,所崇重的师徒关系如父子似主仆,给师傅端茶送水、提礼信做家务等都是断不可少的。但我不懂这种人文习俗,一应同志关系待之,结果没有师傅愿意收留我,师傅不收的徒弟厂子也留不下,那时的行帮戒律就有这等的厉害。
“你愿意当织布保全工么,做我老公的徒弟。”“我愿意。”我看排骨老兄的脸色就知道了,此时不走还待何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