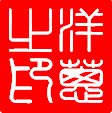我从睡梦中被屋外的叫喊声惊醒,只听到有人在叫喊“孟铁强自杀了”“孟铁强死了”。我猛的从床上坐了起来不禁失声大哭,这时门外有人敲打门页并吼着“你放清白点,你是一样的货色,下一个就是你。”我连忙把被子捂住了头在被子中哭泣,泪水湿透了被里,昨晚批斗孟铁强的情景浮现在我眼前:孟铁强跪在一个扮禾刷上,人们在工宣队的带领下喊着口号,汗水在孟铁强周围的地上滴出一个圆圈,孟铁强紧闭着嘴唇,两眼呆滞、神情木木。我坐在离他不远的地方。批斗会散了之后我回到房间和同住一起的杨三毛说:“三毛,孟铁强今晚魂已散了,可能他活不了多久,要不他精神会出问题。”不料第二天一早便得到验证。想到这里我泪水再次涌了出来。我和孟铁强并无深交,但高中三年在一起学习和生活。我班下放靖县当知青四男二女共计六人,我和孟铁强还有一女同学分在了五四园艺场。自然而然。这种同学关系使我们本不亲密的感情变得亲密起来,这是在远离家乡的唯一亲情,这是在靖县五四园艺场唯一同班的男同学。他离我而去,怎叫我不悲伤,怎叫我不流泪,怎叫我不心中滴血。今天连我哭的权利也没有。悲痛的权利也被剥夺,孟铁强的一切又历历在目。
我初中就读于长沙市二中,初中成绩不错。因为家中兄妹较多,考高中时想考一个好的中专学校。我第一志愿填报了衡阳航空学校,以后的几个志愿全部填报了二中,心想虽然我出身不好但成绩还可以,如果航校不录取,第二批补录二中肯定进不了,我就可以去工厂当学徒以减轻父母的经济负担。没想到在志愿的结尾我填写了一个服从分配,我被分配在五中高六十八班。在五中高六十八班,第一任团支部书记就是孟铁强。班上开第一次班会,班主任宣布团支部书记孟铁强讲话,从后排走出一位一米七八的英俊男生,他快步走上讲台他抹了一下乌黑的头发,白皙的脸,高高的鼻梁上架着一付眼镜,眼镜后面射出有神的目光。他说话有力,神态自若,他的发言迎来一阵阵热烈的掌声,这是一位受同学们爱戴的团支部书记,他的才华溢于言表,我深深的被他的发言打动。
这是一个炎热的夏天,礼堂里全校师生正在开表彰大会。请银质奖章获得者孟铁强上台领奖,春风满面的他急步走向主席台,黑发随着脚步有节奏的起伏。他捧起银质奖章,一脸阳光满身灿烂。他在掌声中作了简短发言,他向领导及老师们鞠躬致谢,向同学们挥动着闪闪发光的奖章。
风云有变。从高二起,五中迎来了狠抓阶级路线教育和狠抓阶级斗争的高潮。出身于资产阶级家庭的我受到冲击,我开始沉默寡言,我走出校门才感到心灵的释放,回到家中和母亲兄妹们在一起才感到人生的快乐。到高三,阶级斗争的风云已密布教区,我深感窒息但又无奈,没完没了的背叛家庭的发言是我的主要任务。我班一个女同学站起来谈背叛家庭,没讲几句就泣不成声,她承受不了这样大的精神压力和折磨,她的泪水发自内心,来自一种恐惧。同样孟铁强同学也不能幸免,他被撤掉一切职务,也和我及那位女同学一样开始无休止的努力的与家庭划清界限。精神的摧残,政治的高压,使我们的心灵不堪重负。但孟铁强在那种环境中仍然发奋学习,仍然出类拔萃,成绩一直名列前茅。
又是编排大型舞蹈《亚非拉人民要解放》。从今天的角度看那不能算是舞蹈,这只是穿着亚、非、拉民族的服装、喊着整齐的口号、踏着有力的步划,做着拯救世界大多数穷苦人民的梦,在台上涌动。难怪演主角的、站前面的一定要出身好的同学。我和孟铁强及出身不好的同学都站在后面听从班委和团支部的指挥。我们认真的做好每一个踏步,一遍又一遍的操练着。说实在的,孟铁强少有文艺细胞,和我一样笨手笨脚。他站在我的右边喊着口号、唱着歌、做着不十分协调的动作,我突然领悟为什么同学叫他孟拐子,原来他确实手脚有点不协调,手喜欢甩动,但从侧面观察他,确实是英姿焕发、一表人才。
这是一堂作文讲评课,怪!今天主持讲评的不是语文老师而是兼任我班班主任的王校长,王校长开口了:黄某某在写作文《背叛我的家庭》后和同学说:今天我向父母又一次泼了大粪。黄某某出身大资本家家庭,父亲解放前剥削工人,解放后对抗共产党领导反对改造。他不但不划清界线,反而用“泼大粪”来形容,难道资产阶级本来不臭吗?……他越说越激动,并开始上纲上线指出:这是对抗思想改造!我低着头,任凭他批判,反正我已说了听天由命吧!我1945年出生,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我只有4岁。母亲是文盲,一天到晚就是做家务带孩子,把8个子女拉扯成人。父亲忙于工作,对我们严肃而不苟言谈,我真不知道解放前的情况。我只知母亲温顺善良,从不与人计较,父亲出身安徽屯溪修林乡的一个穷山沟中,14岁去上海学跑街,后有积蓄举家来长沙发展。发迹后把安徽的所有亲戚从农村接到长沙,送钱送米安排他们工作,这可能是徽商的传统作风。我要写与剥削阶级父母划清界限也只能胡编乱造,写完之后我脱口而出:又给父母泼粪了。王校长激愤的说了一通,拿出孟铁强的背叛剥削阶级家庭的文章读了起来,我仔细的听着,我被他流畅的文句、紧凑的段落结构和朴实的文风所吸引,忘记了刚才的痛楚,心想天才!天才!文章肯定是捏出来的。他和我同一年出生,怎么对旧社会发生的事情那么清楚?肯定他博览群书,潜心研读各类报纸,并记忆超群,方能写出这样好的文章。
很快高中三年过去,我们迎来了高考。高中三年我没有认真读书,我在日复一日的在颂念‘背叛家庭的经文’中度过,我被定为“不宜录取”对象,“不宜录取”者试卷作废、根本不看。估计孟铁强也被定为“不宜录取”。录取发榜了。出身不好的同学除几个被录取湖南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外,其余无一幸免——落榜。
我又遇到了孟铁强,他虽然落榜但仍然神采奕奕。我落榜在情理之中——不求上进、对抗思想改造、学业平平。可孟铁强积极追求上进,学习勤奋,一表人才,成绩一直排在班上前几名。上天无眼,抛弃了一个对国家对社会可以作出巨大贡献的人才。抛弃了一个满腔政治热情,一心跟党走的同志。
我们一起报了名上山下乡,我没有要人做工作。我想让王校长也看看,一个出身剥削阶级家庭的人、一个抗拒思想改造的人同样听毛主席的话,听从党的召唤,奔赴最艰苦的地方。那孟铁强更不用说,他第一个报名。我们带着大红花,在无数饱含泪水的亲属送行中挥动着手,含着笑,坐上开往靖县的大客车出发了
突如其来的一场大火因两个女同学烧稻草灰洗头引发,火势在西北风的呼啸声中越烧越猛烈,几千斤稻草连同附近同学的宿舍被大火吞灭,孟铁强带领大家投入到扑灭大火的战斗中。他不顾一切冲在最前面,救出部分同学的财物可自己被多处烧伤,火被扑灭了。随着这场大火五四园艺场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被烧伤的孟铁强同学送到医院治疗,孟铁强的人生厄运从这里开始。
为了护理病床上的孟铁强,场里派去了初中班的两位女同学。在日夜的护理工作中,两位女同学和孟铁强相当亲密,可这种亲密都是在一个公共的病房当中,都是在人的正常的情感范围之内,都是光明磊落的同学之间的纯真的友谊。出院后,场党支部抓住这一点,以生活作风有问题为由,对孟铁强进行了批斗并免去了他团支部书记的职务。这对一个作风正派的追求思想进步的青年,在当时意识形态中无疑是致命的残酷的打击。
随之阶级斗争的风云又起,天天学习毛主席著作,颂读毛主席语录,背老三篇唱语录歌。孟铁强又一次卷入政治的旋涡,成为阶级路线斗争的牺牲品。分场调整了一位出身好的知识青年任团支部书记。一个历来承受着阶级路线高压和迫害的我对这一切已经麻木,但迫于形势除起床、劳作、睡觉之外就是老三篇不离口,红语录不离手[/size]。
劳累了一天的我正做着美梦,一阵起床钟声把我惊醒。按场部昨天下达的指令,起床的第一件事是振臂高呼毛主席万岁!万万岁!我翻身坐起拚命的高喊毛主席万岁,这一声因刚起床中气不足声音沙哑,定定神又一次高叫:毛主席万万岁!这次响声不错,应该周围的同学能够听到。经过一段努力,声音逐步洪亮,中气也有稳定提高,我如阿Q一样脸上透出得意的微笑!
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孟铁强第一个贴出了炮打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蒋书记的大字报《五四园艺场向何处去》,同学们围着观看。大字报越来越多,园艺场同学开始关注外面的“革命”形势,随着文化大革命的深入,“批蒋”的斗争也在深入发展。
一天傍晚,我找到孟铁强,在落日的余晖中两人向艮山口戈村方向散步而去。默默的走了一段,我开口了:“孟拐子,为什么要紧追蒋书记不放?难道蒋书记有对我们知青不好的地方吗?蒋书记出身苦大仇深,家中几代赤贫,解放初又是全区民兵模范,我们这样的出身有什么必要对着他干呢?这样下去,文化大革命结束他不会秋后算帐吗?我们将得到什么结果?”孟铁强一下激动起来:“我们是响应毛主席、党中央、中央文革的号召,向一切走资派开火、蒋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我们要打垮他踏上一只脚叫他永世不得翻身……。”他挥动着手活象一个对着千百万听众演讲的政治家。我叹了一口气,知道他听毛主席话,跟共产党走,在任何政治斗争中冲锋陷阵是他的一贯作风。那怕自己被阶级路线迫害,他也要拥护阶级路线;那怕自己被阶级斗争所斗争,也支持狠抓阶级斗争。
一个正直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气味的人,一个被意识形态愚弄了的人,一个不可救药的盲目崇拜政治的信徒,这是孟铁强同学的真实写照。
一个单瘦精干、在尖尖的脸上时而挂着微笑的人在我视线中出现,这就是蒋书记。凭良心说,蒋书记对我们知青不错,黄师傅和周师傅在他的带领下管理着我们分场几十个知青。我从这几位贫下中农身上感受到靖县山区农民的淳朴和善良。刚从一个阶级斗争激烈的环境中来到一个虽然又苦又累的农场,但我没有了精神上的压力,我得到心灵的解放。文化大革命进一步深入发展,蒋书记也“靠边站”了,他被安排在猪场喂猪。我们各自为阵,自己管理自己,一部分同学开始回城,一部分同学外出串连,食堂也没有了专人搞饭菜,留下的人轮流进厨房想吃什么自己弄,真是过着神仙般的生活。库房里有茶油、菜油、大米,鸡场里有种鸡蛋,地里有蔬菜、花生、西瓜分场还有几条日后成为佳肴的狗。把茶油烧半锅,鸡蛋打了一脸盆,搅均后待油烧红,缓缓的倒入,居然炸出一盆与挂面一样的蛋丝,真美味极了。去艮山口戈村那口深塘钓鱼也是一种奇趣。不用钓竿用一根尼纶线捆着一个鱼钓放入塘中就可以不停的拉上鱼来。这鱼,头大身小。是当地农民不知喂养长年饿成这样。只要有鱼饵它必上钓。想吃鱼钓来一大盆。想吃狗肉,打狗。一连打了几只狗,大家吃狗肉。我们喂有两条大黄狗,又高又大,弹跳能力极好,大的叫大黄,小的叫小黄,非常听话。大家舍不得打。它一天到晚围着我们也给农场带来了乐趣!一天两只都失踪了,听说是被过路的车带走的,大家悔恨不已。早知如此被人家吃掉还不如自己动手以饱口福。我和杨三毛抬着箩筐去了西瓜地,挑选半天摘来十几个不大不小的西瓜,这是我们亲手种的,瓜真甜,每天吃一个。不干农活‘天天饮食’乐哉!悠哉!
今天我去猪场看了一下蒋书记。他一个人在喂猪、打扫卫生。他见了我笑呵呵的,看不出他是一个被打倒的走资派。可能他从小干农活,把劳动看成是第一需要。所以他根本不背包袱,比在位还快活。现在双方谈的都是喂猪的问题。他表示感谢我来看他。我本来想安慰他几句的,但现在看来两人谁都快活,谁也不用安慰谁。
文化大革命向纵深发展,五四园场也随着文化大革命进入了另一个阶段。
自由的人、毫无约束的人一部分回城去了,一部分出去串连。 留下一部分男同学介入了当地的‘革命’斗争,和县城造反派挂上了勾。 有了各式武器,知识青年更神气了。县里造反派也知道这批人比较玩命,开始组织五四园艺场的知识青年北上了,北上攻洪江、打安江。重型武器也不少。前方传来了消息。县“湘江风雷”一同志在攻打洪江时被打死了。又传来消息:知识青年一同学大腿中弹,这一弹打醒所有的知青,原来生命如此脆弱。原来武斗也要死人。三思之后大家撤了回来,不干了。还是去串连,回家,要嘛就在农场里玩玩。文化大革命接近尾声。五四园艺场武器装备齐全,可大家也不知今后道路怎么走,日子怎么过。传来消息:县里成立了工宣队。派几百人包围了农场。我们开会碰过几次头:是缴械还是对着干?他们有武装部的武装人员,我们有北上武斗的勇士和大量的枪支弹药。几经思考。大家还是作出了一个正确的决定:交出武器,接受审查。
人员都叫回了农场,农场恢复了过去的体制。人们又听敲钟,起床,吃饭,睡觉。一个知青被抓了,又一个知青被抓了!一共抓了六个。天天批斗会,孟铁强是第一要犯,挂尿桶,挂牌,游街。这是家常便饭。知识青年人人自危、个个检讨。几个被抓的天天轮流被批斗。
今晚轮到批斗孟铁强了。食堂里饭桌早已搬开。蒋书记和工宣队都坐在前面,他们上方扯着一条白横幅:打倒现行反革命孟铁强。墙壁上贴着无数的标语。批斗一步一步进入高潮。孟铁强脸无表情,带着眼镜跪在扮禾刷上,时间太长,双膝开始红肿,但他并未挪动。 他象木头人一样,目光呆滞。时间太长,孟铁强的汗水已在地上滴出了一个圆圈。批斗进入高潮,孟铁强被欧打,在被打的那一刹那,孟铁强脸上肌肉颤动,但马上又恢复到木然的状况。批斗会开得很晚,大家都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到各自的房间。
然而第二天孟铁强走了,带着对毛主席的热爱,对党的忠诚,对“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的雄心壮志,带着“反革命”的头衔,离开了这个世界。
我和杨启平、陈启瑯、杜均汉在审查结束后被分配在离贵州省十几公里的大山深处大堡子公社防江六队。父亲为我在长沙县洞井公社白田大队安排了转点。离开靖县之前,我和蒋书记在县城一个小餐馆进餐话别。双方进行了长谈,蒋书记告诉了我,我是抓走六人之后工宣队内定的第七人。由于他的努力我幸免于难。谈到孟铁强他丝毫没有内疚。我看着他,心里想:蒋书记,包括那些对孟铁强动手的人,都是极左路线的受害者。让上帝宽恕他们吧!
早有粉碎四人帮的拨乱反正,早有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主席的政治开明作风,孟铁强必定是一代英才,必定能够为党的事业、为社会主义建设、为实现四个现代化发挥巨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