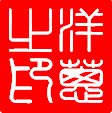我们下到队上那时节,八公大概已近四十岁了,一只偌大的酒糟红鼻子赫然扣在脑门下面,见谁总是笑嘻嘻的。陡然看到大城市里来了一大群年轻伢妹子,而且今后还要在此安家落户,他觉得十分新奇和不解,一段时间成天围着我们转,我们之中谁要和他搭上了腔,他即刻受宠若惊,也不管你受不受头,搓一根喇叭筒先递过来,大有一副相见恨晚的模样。
村里人又称八公为八先生,在石氏家族里是成字辈,辈份有蛮大。虽然只读过几年私塾,写出来的字跟得猫呕的一样,实在不敢恭维,但摆起龙门阵来却是前三十年河东,后四十年河西,一路路的。
八公家里穷的叮铛响,真的叫做是家徒四壁。在农村房屋是根本,山里人苦省苦扒也要打造一栋榫木结构的象样的房屋,他家却是少见的土墙垒起的低矮的茅草屋。里面就一间大统房,走进去乌漆抹黑,只有玻璃天瓦透下一扇光映在布满灰尘的灶台上,零星摆放着几只似乎总冒洗过的蓝瓷碗。至于其他地方有些什么,始终没有印象了。
要讲八公死懒好恰,不思进取还不至于。平时出工可以整天看不见人,偎在漆黑的茅房草屋里睡大觉,我们有时碰见他:“八公,今天又妹做事罗?”他总是有气无力的回答:“妹乖哦!”“妹得饭漆哦!”搪塞过去。但是只要关键时刻队里有大事,比如说排涝抢险,出圈挖塘,或与邻队论理什么的,他总能出现在关键的地方,就象换了一个人,吆喝声比谁都大,什么苦活累活都舍得干。再如当时的所谓政策条文,或乡规民约,他都背得滚瓜烂熟,随时能旁证博引,信手掂来,辩得周围的人大眼瞪小眼,所以很多事队里还真少不了他。他的辈份又大,对他经常不出工也只好睁只眼闭只眼,怕就怕他月月找队上借粮食,反正都是只借不还,到了年底最终补助一笔充数了事,来年开春这样的情节又会周而复始。
说来也巧,不知是生性如此,还是后天的影响。八奶也是懒出了名的,而且比八公多了一个顺手牵羊的“本事”,手脚之快,令人咋舌。比如有一位大娘伙才纳了一半的鞋底,一眨眼连簸萁里的带手里的一只都被藏到谁也想象不到的地方,这时八奶定会热心地张罗寻找,比自己丢了东西还急。谁要怀疑她或抓了现场,那就象炸了马蜂窝。她可以拍手跳脚骂上几个钟头不重复,精神好得不得了。
八公对改编以前当土匪的事从来是缄口不提,而对改编后开拔朝鲜战场打美国鬼子的情形却是讲得眉飞色舞,泡沫横飞。说自己在一次肉搏战中干掉了三个美国鬼子,说着还撩开衣襟,露出从腰到背一溜长长的刀疤,指着说这就是见证,看到他急切的样子,我们深以为然。有一回竟说一颗机枪子弹从下往上把他的帽檐打飞,头发都烧焦了,我们都说不可能,把他急得捶心顿足,原地团团打转。
时隔三十多年,这次回靖县见到了八公,背已经佝偻了,显得苍老了许多,神气却还是有如昨天。他一眼就认出了我,抓住我的手使劲地摇了又摇,却无论如何认不出周平来了。
他十分得意地把我们带到了鸭冲前面一栋榫木结构的大屋前,这回轮到我们吃惊了,想不到他老人家晚年还能住到以前做梦都想象不到的新屋,真是世事难料啊。
原来八奶和他那严重营养不良的大崽在我们走后不久先后病故,但在他们五十多岁时,八奶病故前几年,又为他留下了一个十分健康聪明的满崽,他一个男子汉在临近垂暮之年,屎一把尿一把挣扎着把满崽抚养成人。
他现在伴着满崽住,而且他的满崽对他特别孝顺。
他的满崽不在家,但看到房前屋后打理得井井有条,以及眼前的手扶拖拉机、抽水机、摩托车,我们猜想那一定是一位善于经营的好手。
八公的晚年终于有了一个好的归宿,他是值得庆幸的,我们临走时再三祝福他。
我们在八公家作客. 私语兄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