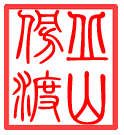樟树下的悲情 (二)
那是一个火热的夏天。我们妇女包工锄这一大片棉花草。当时,潇潇是作业组的记工员。傍晚收工的时候,潇潇和队长老婆吵起来了,我走近一看,队长夫人正气呼呼地说:“你自己锄的地上也找得根把草出来呐!莫逞狠!”“我锄得不好我返工,你锄得不好也得返工!”说完潇潇顺手在她的棉花厢子里拔出一把草来:“你看,这哪象锄过的样子?”“你就会跟我们贫下中农过不去!”队长夫人看也不看边说边扛起锄头回去了,留下我和潇潇气愣愣地站在那里。晚上记工分的时候,潇潇提出要她返工:“大家明天可以到地里去看看,该返工的就要返工!”“你找什么岔子!”队长夫人大动肝火:“你根本就没资格当记工员!你是什么货色以为我们晓不得?”她扫了一眼屋内发出一阵冷笑,小屋子里一下子哗然了。“做得不对就该管嘛!”屋角里响起了不平的声音,我一看,是我们队里的回乡青年张良。潇潇并不示弱,提高了嗓门说:“我是什么人?我是知识青年,是毛主席要我们下来的,错了?维护集体的利益,也错了!”队长见状马上出来打圆场:“好了好了,潇潇讲得对,明天我们再去验收一下,凡是不合格的,都返工!”不知谁在底下咕哝了一句:“好大的口气哟,哪个来接受再教育?呵?”听到这话,潇潇再也忍不住,丢下记分本跑了出去,我急忙跟去,只见她跑进宿舍伏在床上抽泣,经我一番劝导,她才抬起头说:“这个队长的一家,是谁也惹不起的,四清的时候,我们批判过他,他们不怀恨在心?说知青来扯薄了社员的被子,不就是他们放的风?现在又当权了,我们有好日子过么?”……第二天,我们重返了棉花地,虽然最后潇潇闹赢了,但记工员的差事她硬推给了我:“你干合适些!”事后,我还老埋怨她没有活学活用主席著作,遇难而退,现在回想起来,我当时的学用,也没有“立杆见影”……
转过弯子,我继续朝木园走去,在一片矮树丛中,高耸的樟树仿佛张开手臂在迎接我,那里是我和潇潇经常谈心的地方。潇潇,原谅当时比你还单纯幼稚的挚友吧!青春的小河,在生活的礁石面前,激起了那么多令人心颤的浪花……
随着队长安排的劳动越来越不照顾,潇潇的思想包袱越来越重了。白天,在男人们裸身只围一条帕子的稗草田里,经常也有潇潇一身泥一身汗一身石灰的身影;黄昏,通往大樟树的那条小路,踏满了她徘徊的脚印。社员们对她也有看法了,说她劳动不如以前,也不大爱和别人接触了。床头一大叠书籍成了她唯一的慰藉。有时深夜,她还独个儿坐在溪水边,唱着那支苏联电影歌曲:“当年我的母亲……”,我多次找她交心,奉劝她甩掉家庭包袱,摈弃小资产阶级思想情调,当文化革命的闯将,她就是死心眼。她心底里,我也知道,很痛苦,很迷茫,怀疑我们这条路到底走不走得通。她变得越来越孤僻了;而我,当时倒越来越走红,大队领导一时头脑发热,还让我当了一阵子本地红卫兵组织的小头目。我的革命热情越高,就越恨她这块铁不成钢。“你革命!你好!”她总是以这样的舌剑招架我的唇枪:”什么红卫兵!组织不需要我,我也不稀罕它!你革命,我认命。”一个从不疑神信鬼的知识青年如今也相信命运了。她看淡了我们的友谊,命运却向她抛来一束爱情的山花!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