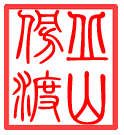樟树下的悲情
月亮出来亮旺旺,亮旺旺,
看见月亮想起我的……
——云南民歌
暑假,我背着一个小挎包,又回到了久别的第二故乡。
这是靠近广西的一个美丽的小山村。记得当年刚来时,站在那座吱吱呀呀摇摇晃晃的高高木桥上遥望村子,她象个仙岛,迷朦烟波托起的一叶绿洲,常见的飞檐楼阁都隐藏在繁茂的树林之中,显得分外妖娆;如今我登上这水泥拱桥,小村子已裸露出来,青瓦农舍旁多了两幢红砖屋,变化不大;村后那棵庞大的老樟树挺拔如旧,白云在它的身边缭绕,远山含黛,浅水荡碧,我迈着轻快的步子,又回来啦。
这是我招工后第一次回来。乡亲们都特别热情,香喷喷的新米饭,香酥酥的槟榔芋,从不喝酒的我也品了几口甜甜的米酒。闹腾了一天,直到半夜的月亮爬上山冈,奶崽们都睡了,我才一个人悄悄地走了出来,我睡不着。一 行杨柳树沿着小溪蜿蜒向村后延伸,月光下,清鳞鳞的水面上轻轻地覆盖着一层薄霭,我捧起井水喝了几口,一阵凉风吹来,耳边仿佛又响起了那首《小河淌水》:“月亮出来亮旺旺,亮旺旺……”,而潇潇,最爱唱这支歌的知友,却永远离开了我,长眠在那棵老樟树旁。今晚,我又来了,缓缓的脚步不由自主地顺着这杨柳登上了村后的小坡,随着团团树影,石墩的移动,我的思绪飘拂到那动荡的岁月……
当初,我们都是一些血气方刚的年轻人,看了报纸上讨伐“三家村”的社论,也爱发表一些“金猴奋起千钧棒”式的高论,以“个个都是批判家”自豪。然而,正是这个时候,潇潇沉默了。她收到姐姐一封来信,得知父亲“畏罪自杀”,罪名是“反动学术权威”。因为她母亲早就因“性格不合”离了婚,现在唯一的亲人就是在长沙教书的姐姐了。我很同情她,但认为自己更有责任帮助她,帮她走出阴霾,与家庭划清界限,勇敢地与旧的习惯势力作“彻底的决裂”。我们经常谈心。她固执地认为,当前许多做法不对:“高帽子”满天飞,“棍子”到处打,今天楸这个,明天轰那个,从上到下的干部,学者,轮环着挨批受斗,二十一种人就更别提了!我说,这是史无前例的一场大革命呀,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绘画绣花,是造反,是你死我活的斗争!斗争中的伤害,甚至运动中的偏差,也是不可避免的。最重要的是我们必须多读主席著作,紧跟上面的指示精神办。我劝她不要小资产阶级温情主义,她却反复强调:“你出身好,一帆风顺,难以理解我。”这样,我们的谈心往往不了了之。
她家的事不久就在社员们之间传开了,闲言碎语象一块沉重的石头压在她的心上。田间地头,她的歌声消失了,批判“大小邓拓”的会上,再也听不到她的发言了。凭着我俩的友谊,我们还是行影不离,一同出工,一块儿学习,在广阔天地这个革命熔炉里,我相信,旧的东西总会被淘汰,一时软弱的人也会磨练得更坚强。
我一边走,一边想,忽然,一只受惊的小鸟飞檫而过,摇曳的树杈下洒满了点点月光。我定眼一看,已经来到了村后一条通往广西的乡道。左边是木园,右边,是队里的棉花地,不正是这块棉花地,曾洒满了我们的汗水,也滴落过潇潇屈辱的泪水吗?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