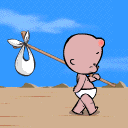俄罗斯情结
*
常和友人聚会,大概因我有意无意间不太合时宜的一些流露,友人们笑我是个前苏联迷,说我知道的外国就是前苏联,会唱的歌曲都是前苏联歌曲。我不否认,并很愉快地接受这一调侃。须略加解释的是,如果我有一种这样的情结,准确地说应该是一种俄罗斯情结。
其实何止我一人独有这种情结,上世纪中叶出生的一代人,或多或少都具有这种情结,因为他们都受到太多俄罗斯文化的熏陶。以我们这些上世纪四十年代末五十年代初出生的人来说,除了民族文化,所接受的外来文化主要就是俄罗斯文化。我们还在上小学时就开始读《金鱼和渔夫的故事》,上中学后,会为一篇《海燕》而激情澎湃。慢慢地,我们会看莱蒙托夫,会看法捷耶夫,然后又偷偷学着唱《红莓花儿开》和《山楂树》。而我们熟悉马克·吐温和德莱赛,会唱《苏珊娜》和《老人河》,则是很多年以后的事了。俄罗斯文化的浸润有她特定的历史原因,凡过来人想都知道。即使到上世纪六十年代初,这种浸润也没有因两国关系的破裂而干涸,即使到文革荒唐年代,知青们仍然把残破的《复活》和《狄康卡近乡夜话》带到知青茅屋的煤油灯下,或孤独一人坐在田埂上唱那首忧郁的《田野静悄悄》。那个年代距今天虽然似乎很遥远了,但她已经融进了你的血液之中,或者说你的骨骼有相当一部分是由她铸造,你如何能释怀?
于是我们一班同龄人仍然常相邀在一起,或到小巷深处一幢民宅里伴着一台古旧的钢琴,或到郊外寻一块青青草地,去哼吟那温馨的回忆。歌本大家都带着,但无须翻它。无论哪首歌,只要有人带头唱出几个音符,大家就立刻轻声应和。曲谱也许不那么准确,但不要紧;也许整段的歌词都不记得了,也无所谓。不是说有残缺的美吗?唱完歌,我们或许还会谈论一下俄罗斯的文学和电影,当然,也许还涉及一下乌克兰,比如说舍甫琴科。他会问,还记得〈船长与大尉〉吗?你会说,那本〈罗亭〉你至今还未还我;她会提醒你,你在农村曾把那〈木木〉的故事讲给低年级的女同学听,听得她们潸然泪下,她会窃笑,揭发你曾是当年〈叶尔绍夫兄弟〉里的阿尔连采夫。然后又有人提起了邦达尔丘克,那是因为〈奥塞罗〉和〈一个人的遭遇〉,你会补上一句还有斯特里仁诺夫和贝丝特里斯卡娅,因为你忘不了〈牛虻〉和〈上尉的女儿〉,忘不了〈静静的顿河〉。夜已深沉或斜阳西下,大家都安静下来,任思绪轻盈飞翔,飞过俄罗斯茫茫大草原,飞过白桦林,飞到伏尔加河畔。
年逾六十之人,因一段共同的人生经历,把一段异域的文化珍藏于心,挥之不去,是一种情感的积淀,或许还是一种带些许伤感的怀旧。还请谅解。确实,那个年代离我们已经很遥远了,但像世界上所有的民族都在传承自己的文化一样,俄罗斯文化今天一定仍在闪烁着她的光芒,虽然由于历史的原因,在上世纪后来的几十年里,这种光芒要透过太厚重的云雾才能射到我们身边,以至于有些若明若暗。今天再唱俄罗斯歌曲似乎有些不合时宜了,因为有了太多的快男和超女,但我们还会唱下去。我们会努力进入今天这个时代,但我们不会忘却过去的那个年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