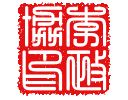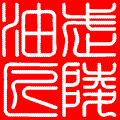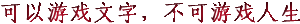声名狼藉
1.上午。课堂上。
“操吴戈兮被犀甲,车错毂兮短兵接。旌蔽日兮敌若云,矢交坠兮士争先。”老师抑扬顿挫,拟古风吟“国殇”,惊天地恸鬼神。
我魂魄神游,像苍鹰俯掠战国时期的秦楚战场,车轮交错短兵相接,旌旗蔽日乱箭交织,披甲操戈呐喊厮杀,血海尸山苍天荒原。
突然一下奇痛,魂魄跌回课堂上。回头看,庆生正在挤眉眨眼努嘴;往下看,腿肚子上还揣着他的鞋印,脚尖一个足球蹭磨着;往前看,七八条腿伸展在课桌间道上意作拦截。我抬脚挑射,那球径直飞过七八排仰视的人头,“咚”的打在了黑板上,老师瞠目结舌,像面对一计冷射而猝不及防的球门。
如今已经是什么年月了,轰轰烈烈地文化大革命掀开了序幕,“停课闹革命”的口号开始叫响,“师道尊严”被打翻在地踏上了一支脚。
哄堂大笑,这是一群大院子弟,他们的父辈原曾也不过是啃土坷垃的农民,就是因为一个穿越时空两千多年的血性呼唤:“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于是撂下锄头端枪在手,打下一个血红江山,封侯拜将,挣下了顶戴花翎,然后为了后继有人而狠下气力,生下了现在这一群荷尔蒙燃烧的虎犊狼崽,他们急欲冲到大风大浪中去撒野,经风雨、见世面。这种激情孕育着一场席卷全国的“红卫兵运动”,其给历史留下的惊恐,绝不亚于2000多年前秦朝的“焚书坑儒”。
讲台上老师的表情转向冷漠,齿间咬切出两个字:“下课。”
人潮涌动,奔腾出教室、下楼梯、出教学楼、冲溃初中部校门,狼奔豕突过马路。马路那边是高中部,“过马路”一词在过去总是被老师拿来说道,喋喋不休:“初中生的目标就是过马路,考本校的高中;高中生的目标就是过长江黄河,考清华北大”。现在再这样说就是脑壳进水,现在中学生毕业有四个面向,有哪一个面向是读书的。而我们现在过马路是去食堂抢饭吃,争先恐后是为了“吃七桌”,原来食堂的饭菜定量安排是8人一桌,而就餐的人数不一定是8的倍数,于是就有了7人吃8人份额的机会。那是个物资匮乏的年月,饥饿陪伴着我们天天向上。
2.中午。食堂里。
一群初中生狼群般地霸占瓜分了饭桌,敲盆子打碗喊开饭,千呼万唤。但是,更大一帮高中生堵住了饭菜窗口,拥挤成推,这可真是奇了怪了,高中生本是更为凶猛掠食的动物群落,而现在却要饿着肚子干革命,搞什么教育革命大辩论。
几百号人拱蛆一般堆拥,混乱之中两派大辩论,但见一人蹿上饭桌大声疾呼:“革命的生工员师战友们!革命的生工员师战友们”!呓?这厮出言怎么这么别扭,莫非是饿得脑筋急转弯了?平常的称呼都是“师生员工”的排序,怎么到他这就颠三倒四了呢?
我脸上的问号竟被一人识破,靠近身来好为人师释疑解惑,那厮循循善诱,先问毛选“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读过没有,再与我重温光辉思想,活学活用联系实际。对呀,“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在现时期仍然是中国革命的首要问题,譬如在学校搞文化大革命,主力军是学生,团结的对象依次是工人、职员或教师,打击的就是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深刻道理细心领会,拨云见日、茅塞顿开,只觉得心眼里头热乎乎。此公名为章正凡,是高中部派往我班的辅导员。
章君,能人也,从临募毛主席诗词手迹开始,最终练就一手绝活,不论何人笔迹都能仿真,复印一般惟妙惟肖。1967年的2月和3月,国务院两次发文叫停红卫兵大串联。但哥几个刹车不住仍惦记着北京天安门,于是乎扮装“受迫害知青赴京上访代表”,到了“湖南省革命委员会接待站”,挤进人头攒动水泄不通的窗口前,忽悠去北京的免费车票。几天下来正当万般无奈之际,救星章君蹙上前扯过状纸大笔一挥:“请批三张赴京车票,刘善富”。刘善富何许人,47军副军长,湖南省革委会副主任是也。我拿着批文蒙五关混六将,赚得车票去了北京。
章君,高人也,高瞻远瞩先人一步。上个世纪80年代末,“干部队伍年轻化”之风乍起,此公主动从经委副主任位上急流勇退,获一闲差为侨办副主任,随即走出国门联谊爱国华侨搞统一战线,兼得领略全球万般凉热,阅尽世界无限春色。待到党政官员熙熙攘攘挤破国门之际,公费出国旅游之开山鼻祖章君也者,又在正襟危坐说廉政。而今在“博鳌”混一国际贸易促进会之干事,嵌金白领,红白无间道。敢问能拿捏世道于方寸之间者,惟章君是也。
时空转回食堂,此时我的目光已被桌上的那位勾引过去,但见一身黄卡其军装,腰扎一根军用皮带,正宗牛皮的且宽,皮带头及皮带扣正宗黄铜的且大,这是50年代军官授衔时的制式服装,浸渍着令人敬畏的历史感和贵胄气。其后的军装制式如国防绿和人造革等,浅薄俗气不能比拟。
60年代的明星照是雷锋像,军帽罩住后脑勺,帽檐撩起展露大额头。那厮反其道,一顶军帽齐眉扣住,帽檐下压,遮不住的双眼激情燃烧,他像列宁在1918那样身体前倾,舞动双臂登高而呼:
“我们学校现在成了一个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封资修的独立王国,把一场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搞得冷冷清清死水一潭,难道我们不应该起来革命?”
“天下者,我们的天下;世界者,我们的世界;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我们就是要手榴弹爆破筒炸药包一起丢上去,炸出一个红彤彤的新世界!”
“现在,我要宣读一份告全校生师员工的公开信”,下面的喧嚣稍停,无数的耳朵竖起,那厮开出群众运动的项目有十几项:停课闹革命,大字报、大批判、大辩论、大串联、破四旧立四新等等,他把手臂高举,每念一项就往下砍一下,随即众人就吆喝一阵,有喊“好得很”的,有喊“好个屁”的。那厮高呼:“要是好派的你就站过来,要是屁派的就滚你妈的蛋”!这话好像是挥动鞭子赶羊群,好派屁派划线站队,我们一声欢呼,跟着往里扎堆。
猛然,一声高频交流啸叫刺穿耳膜:“严双福,你是那里滚出来的蛋?”循声望去,一女生凛然跨立,身旁另有一妞胸脯挺高。这是姐妹俩,爹妈所赐的玉姓芳名太一般化而难得记住,得幸文化大革命给了换姓改名的权利,于是她们的名声大振。尤其是那些挨过打的老师同学们,40年过去后的今天,只要头皮发疼腰伤发作,两个赫赫的名字就会蹦出来,一个叫“枪出政”,一个叫“枪出权”,合起来就叫“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当然比她们叫绝的还有,有兄弟俩一个叫“钟共”,一个叫“钟央”,连起来叫就是“中共中央”。
那姐妹俩的打扮,和桌上那位叫严双福的一样,都是一身黄皮,不同的是那根皮带在手里攥着,皮带头敲打着桌面。
那位叫严双福的跟我有缘,一个月以后学校成立红卫兵组织,他是我的头。三个多月过去后的一个冬日,严头紧急召见我等,说是工人造反派要封湖南日报,我们红色政权保卫军的战士要誓死保卫党的喉舌,然后率领我们跑步向前。这时湖南日报社门前已是人山人海,两派对峙互相冲撞打派仗。还有十几辆卡车架起了高音喇叭,相互对攻打宣传战。严头钻进一辆卡车的驾驶室里,招呼我们爬到上面去喊喇叭。湘江那厮见麦克风就上瘾,一把抢过不歇气的喊“湖南日报封得拐,工联是我崽!”我站车头紧紧绷住路线斗争那根弦,提高警惕四下张望,心明眼亮看得真切,分明是一群工联战士头戴柳条帽手持短铁棍,气势汹汹撞将过来。来者不善,形势万分危急。庆生忙叫快撤,湘江喊得性起哪里肯撤,只顾要喊“湖南日报封得拐,工联是我崽!”话未落音便戛然而止,只见一双大手一把咔住湘江的颈脖,一下连人提将起来,举起铁棍只往那厮的肉屁股上狠打,湘江啊哟啊哟悲声大作。而我们一干人等,则像小鸡一样被拎着扔了出去。
湘江那厮有种,都到这份上了,还硬充麦霸死守播音权;只是屁股一打歪,那口舌也就转了调,喊出的口号换成是:“湖南日报封得好,工联是我爷!”“湖南日报封得好,工联是我爷。”严头这时候踪影全无,却似人间蒸发。等找到他已是新旧世纪交替之后,那是在一次会议上,这厮主席台上口若悬河,我依然在下深情仰望。
现在严双福站在桌上拍肿胸脯,“我是革命军人子弟,老红军生下的蛋”。桌下的女高音犹如瓷片刮玻璃:“就凭你爬女生澡堂那德性,你还算是拉出的蛋,是放出的一个屁吧?”严双福恼了,倏地一下抽出了皮带。没想到更猛的还在后头,但见一群女生全部站了出来,齐刷刷地一色黄皮,挺起胸脯像争着百米冲线,齐刷刷地攥着皮带。旁边有人喊起“要文斗不要武斗”。
天下大乱就是形势大好,嗜血天性把我们兴奋起来,好人打好人,误会;坏人打好人,光荣;好人打坏人,活该。我们高唱“说打就打,说干就干,练一练手中抢,刺刀手榴弹。”
扎堆的人越来越多,身着黄皮的都往前挤,一场大辩论变成了军人子弟大联合,其他人众则边缘化。文化大革命演绎世态炎凉,反映不同身份的人群上,且以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逻辑,体现在他们后一代的境遇中。即将开打的武戏给搅黄了,我们悻悻地离开了食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