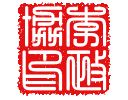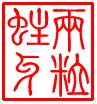《岁月蹉跎之三》
田 佬 倌
——邓晓———
公元1968年12月,文革中抽疯的城市掀起了上山下乡运动。我等五个同学兔子一样蹿到洞庭湖滨的沅江县插队。未过一年,那四个同学又像兔子一样蹿回城市,剩下我这个兔子趴着不动不挪有四年,四年时间结交的第一个农民朋友就是田佬倌。
一.田老倌其人
沅江发源于贵州都匀县云雾山,
田佬倌是万千勤劳乡民中的一个。那厮四十多岁蛮出老,原本周正的一张国字脸,就因皱眉眯眼耸鼻撅嘴等,变成了揉搓过的一块抹布。且喉咙里扯风箱,不停地咳嗽,咳得身子佝偻着,眼屎鼻涕脓痰一把把的揩在胸襟上,时间一长起了硬壳,太阳光照下晶莹眩目。孤寡一个,又是病壳子,作田赚的工分不饱肚,多施土法术治病祛邪,撮饭屑子打秋风聊补饥寒。
垸子里阡陌纵横整齐划一,状似棋盘;长堤上农户建屋,屋挨屋沿着堤势一字排列,形如长蛇。湖区一坦平原无遮拦,大风起兮肆无忌弹暴虐恣睢,那雨不是从天落下,却由狂风挟裹横扫过来,直叫那长蛇扭曲挣扎于呼啸之中,多少茅舍被卷起飘零,风中起舞雨里哭泣。风势雨劲最威猛的要属堤坡头风口处,在此建屋莫若是找死,我是后来才知道的,湖区农民自懂事起就知道,而田佬倌的屋就趴在那里。他不是脑壳浸水,而是乡村的丛林法则使然,弱者别无选择,只能认命。那是一间仅能容身的睡房加灶屋,矮塌塌的像个的蘑菇,歪长斜出。
田老倌一天早起,发现他屋前的上风口处动起土来,那里要盖一间知青屋。田老倌哪里肯信咸鱼翻身,于是天天做死地掐大腿肉,每每地痛得呲牙咧嘴骂娘不止。直待看到那知青屋赫然伫立,把那蘑菇屋严严实实掩在其后,有了遮风避雨的真实感受时,那厮才找到了确信。
田佬倌常怀感恩之心到知青屋,老鼠一样的来去悄无声息,瞅个冷子便摸一两张废纸卷烟抽。那时我等五个知青热闹非常,何曾留意过他的存在。等到同学们都兔也似的蹿回城后,孤单的我才开始和他有了话讲。
那年月时兴忆苦思甜,我向田老倌访贫问苦,那厮便说,人人都说黄连苦,我比黄连苦三分哩!
我说田老倌你讲具体点,那厮就说,我咯一世受人欺还犹自可,连路上碰到的鸡都不让路,还敢啄我哩!
我说田老倌你讲正经点,那厮则说,要诉起苦来呀,那真正是诉不完的苦;远的不讲,就从解放后讲起。
我说田老倌你莫打乱讲,那厮颈上青筋一暴,发起犟来不信劝,就是要打乱讲。思甜,就说搭帮有了知青屋,保住了他的茅屋子不再被风刮跑;忆苦,便说我咯一世人就是命苦哩,养过堂客带过女,都跟人跑了,最后还是孤寡一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