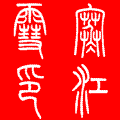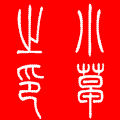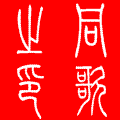欢乐“鬼”故事
我们下放到安乡农村,遇到过很多有趣的事,在那艰苦环境中这些趣事经常用来调节我们苦闷的神经,使我们暂时忘记忧郁、苦恼。
农村几千年的封闭,人们习惯了贫困,文化的落后滋生封建迷信的温床,与世半隔的现实使得鬼神的地位根深蒂固,不经意的鬼神故事,不出半天可传遍全村,而科学技术的传播,强推三、五年都疑惑重重,不改初衷。大家都信鬼,就有鬼存在了,加上那些“亲眼看见”的描述,使很多人怕得夜不出户,黑不单行。
我们队队长是典型的怕鬼,他身材魁梧,瘦瘦精精,人称筋骨人,干起农活,浑身是劲,苦力、难事从来难不倒他。一百七、八十斤担子,健步如梭,挑二担起叠的水毛谷,可在田里小跑。三百六十天,从来不休息,大年初一“开门红”,他一清早就跳在刺骨的水中翻粪氹,不争全队最高工分他誓不罢休。
他有名的怕鬼,生产队‘双抢’期间,每天2:00就要起来出工,唯一的闹钟放在沙阳床头,定格在2:00起闹,而队长每天比闹钟更早地起来‘带头’。他家离我们知青组约百十来米,黑灯瞎火,当他第一脚跨出家门起,就是点燃一根长长的‘喇叭筒’,听说火能驱鬼,先壮一下胆,接着一句高昂的‘汉剧’划破夜空,我们听到了他的小跑步声,离我们住处还有六、七十米,又是一声‘屈家里,我们嘎世嚏波(开始去搞事,行吗)!喊声带着颤抖、夹着跑步声。我们连忙划燃灯盏,沙阳顺手提着铁皮话筒,对着窗外喊道:沙阳四队社员同志们,嘎世哒!扩大了的叫声格外嘹亮地传遍全队,于是家家油灯闪闪,关门吱吱地响,箩筐、扁担伴着步声,开始了一天劳作。屏住呼吸的队长,如释重负地笑了起来,嘿嗨,屈家里,你们真的起得早。搭帮您俺,我一个人起来怕鬼。
开始割谷了,我这桶长发现不对劲,一清人数,还差一个人,不是没人割谷,就是没人踩桶,谷满了又没人挑。我这桶长跑上跳下很不协调。是彭伏喜还没来。我告诉队长,请他叫一下,他要我去,说一个人去怕鬼,我顺便提着沙阳的土喇叭,跑到彭伏喜窗下,嗓门提高八度地喊;嘎世哒,快起来,割谷搞不拢来哒。足足五分钟的狂轰乱炸,笼里的鸡都被吵得咯咯直叫,楼里的猪听到嘲声都开始哄哄吱吱翻身,还没听见人答白。又敲门又打窗搞了半天。从里屋的床上嗷出一声:今天我生日,要休息一天。我哭笑不得,自认倒霉地摸回田里。事后我想,我们队长一身力气,生者几个人都搞他不过(做鬼都不吓人),那死者更不在话下,为何被那些冥冥之中幽灵吓得如此胆小。真有点好笑。
六月初的夜晚,娥眉月在云中时隐时现,沙阳提议每人一支手电,穿双长套靴,捉青蛙做菜吃,吃不完做腊蛤蚂带回长沙吃。一个东,一个西,一个堤上,三个人分头行动,发誓捉光所有出来吃露水的小精灵。我一人来到尾上坟山边,一个个足有半斤重,忙得我搞手脚不赢,蛇皮袋装了一半,那些硕大的牲物,捉了一个,又来一个,引人入胜。忘记了劳累,忘记了烦恼,忘记了坟堆内死鬼作伴,不觉到了十一、二点,这时远处传来刚散会结伴回家的大队书记和二个队长的讲话声。我也想休息一下,伸伸腰,为了调节下心情,想搞个恶作剧来测量一下天天喊‘破除迷信’的书记到底有多‘唯物’。借着蒙蒙月色,我站上了坟堆顶,静等他们路过,我关上手电,在坟顶上忽高忽低扮鬼象,书记看到后,马上停止前进,口里念着:这个杂种的,真的碰哒鬼哒。二个队长早就离他远远的,书记喊道,是人还是鬼!我忍着不出声。他又喊,到底是人还是鬼!我还是不应,而且顺手摸一把泥土摔了过去,他们吓得连忙后退。我正准备笑出声来,他们三人一路小跑说真的碰到鬼哒,唯恐自己跑在最后。我像胜利者似的拖着蛇壳袋回来。真是:蛤蚂撑肚一晌,笑料捧腹至今。
二队知青女某,胆大包天,文革中在男学生都有几分畏惧的情况下,曾‘头戴钢盔,身背半自动步枪,冒着枪林弹雨,行进在红色怒火的战旗下’,在读书时,‘校游泳场晚上11点钟打捞上溺水身亡的学生二兄妹,要招募勇士同车送回离校20余里的学仕桥,我们大胆女二话没说,跳进放尸的车斗,守着被车颠簸而活灵活现弹跳着腿的尸体,护送她们回家。’
下乡后,沙阳二队有个吴泽贵,自己胆小如鼠,还赌别人:凡能用棍子晚上背着二斤猪肉,单身穿过九成弯(地名)坟山(约一里路远)的人,这二斤肉就归谁了。二斤肉,一元三毛钱,相当做五、六天工分的诱惑,使得好多年轻人跃跃欲试,但那毛骨耸然夜色、坟推,又使他们望而却步,都怕被鬼搞一下划不来。我们的大胆女,二话不说,反正自己是近视,看不清什么堆不堆的,背着肉只花十几分钟,成功跨越,无半点不良反应。吴泽贵自认倒霉,好在知码子大吃一餐,一时名声大燥。
又是双抢大忙季节,晚上扯秧到12点,二队那大胆女收工回来,一头泥水,一头臭汗,洗净长发,只求让它快干好早休息。话说离知青屋不远有座‘萝卜沟’烂桥,几根杂树一搭,几块破板一盖,白天过桥都得摇晃着‘步步为营’,一脚踏空,即可招来杀身横祸。加之地处一、二队尾上,人少屋稀,也靠坟堆不远,一般晚上绝对无人惠顾,情愿绕路几里也不走‘野渡、烂桥、孤坟’之地。我们大胆女劳累之极,也顾不了这些,搬着麻凳(小椅子),晃荡着摸到桥上,披头散发,一会梳在左边,一会儿梳向右边,再梳在前面,低着头,垂着发,轻轻梳刮着,尽量散开扩大蒸发面。不远处萝卜沟边住着几户村民,晚上回来,躺在竹床上,拍着扇子,借着微风,驱赶着一天的劳累。无意中发现尾上的烂桥上一位披发女子时隐时现地动着,几根神经一下崩的紧紧的,一身鸡皮疙瘩,一头冷汗,眼睁睁地盯着那烂桥女鬼,细步溜进屋里,关紧门窗,喘着粗气,祈祷厄运不要关顾。渐渐地二岸村民全部撤退,第二天就传出鬼来。笑得我们打六喘。
若干年之后,这些笑谈仍旧做为故事在沙阳知青中流传。这些往事在当时艰苦的日子里,收到了暂时忘掉烦恼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