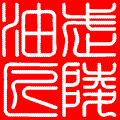何处是归途
北闯安徽
1970年7月,看来是走投无路了,背着“反动知青”的罪名,我逃离了江永县。一想起批斗场上捆、绑、吊、打的情景,总有些惊魂不定。刚一回家,派出所的人又上门训斥,勒令立即回乡,否则即予遣送。晚上,弟弟的同学来敲门,我以为查户口的又来了,吓得翻墙而出,事后才知道是一场虚惊,但仍不敢回家,于是在外过着流浪的生活。
那天,正在街上游荡,碰到同公社的知青李为贵,他一把抓住我的手说:“周哥,这些日了到哪里去了?有人还说你自杀了呢,看到你我就放心了,我正找你有事,走,我们一起吃面去!”
算是他为东,请我吃了一碗光头面。为贵边吃边问我:“我倒有个好去处,你去不去?”“能住有吃就行。”我立即答应,这是我当时最高的生活要求。
为贵的老家是安微省利辛县,解放前,他父亲被抓了壮丁,后来在部队混上了个连长。解放后,由于这段历史,成了管制对象,为贵当然也跟着背黑锅。1964年和我们这些“可以教育好的子女”一起戴着红花下放到江永当知青。前些日了他去了一趟安徽,回到老家三黄寨村。他的叔叔、伯伯是贫农,跟大队公社干部还有点沾亲带故的。亲戚们知道他的苦衷,劝他说:“你父亲当年是五花大绑走的,谁知道绑出了一个军官,真是有点说不清楚。这样吧,你干脆回老家,回来你就是贫农,在家里挣工分吃饭,谁也不会欺负你。”为贵一想这话也在理,在当地住了几天,虽说苦,却还舒畅。看到当地肥皂紧缺,突然想到我曾有办小肥皂厂的念头,特来邀我同去。他许诺,到他家保证我享受“贫农待遇”。我虽觉得事情太玄,却挡不住贫农的诱惑,以前不是有很多人迫于生计闯过关东吗,我何不去闯闯安徽?
下一步就是考虑具体的计划。两人口袋里总共12元钱,这点钱好干什么? 为贵心中却暗有打算。
第二天,我们花8元钱在南货店买了8斤茴香,然后用塑料包了两层,打成一个背包。傍晚我们偷偷溜进长沙北站,看准了一趟往北开的货车,爬了上去。火车经过湖北,车站查得很严,我们就躲在货车里,饿了吃法饼,渴了喝凉水,车子进入河南才松了一口气。这里“外流”的人特别多,爬车已经习以为常,烈日下大群农民坐在敞篷货车上,每人背上一只细而长的口袋,装的是高梁、小麦、玉米、地瓜干,都是出来倒腾粮食的,有的是倒个差价,有的是细粮换粗粮,因为粗粮比较容易填饱肚子。我们也加入了这支“外流”大军。我旁边坐着位大伯,居然隔着塑料袋闻出了茴香味,他拍了一下我的肩膀说:“小兄第,你的茴香能卖上好价钱,每斤七八元钱。”我心里一紧,对方似乎看穿了我的心思:“小兄弟,别紧张,我可不是‘打击办’的,一不抓投机倒把,二不反资本主义,你看车上这么多人倒腾粮食,还不是换点吃的,谁能当上资本家?”我没有答腔,对阶级斗争这些话题,我总是有些过敏,还是李为贵插进来用安徽话和他拉起了家常,我才轻松了一些。到了徐州,转乘汽车来到他家附近的马店镇。在镇上,为贵用茴香换了六七十元钱,有了本钱,心里也踏实了。
“五七牌”肥皂
一到三黄寨村,他的叔叔带我们到了大队部,大队干部知道我们的来意,表示欢迎,但对我们能否制出肥皂却将信将疑,要我们先试一下再说,并把我们安置在荣誉军人李为相家里。李为相在朝鲜战场负了伤,一只眼睛失明了,因此每月能享受一份粮食补助。1960年过苦日子时,他总是匀出一半补助粮食给弟弟,老婆不答应,他一气之下就把老婆打跑了,从此成了单身汉。李大哥热情地接待了我们。他家的房子是土坯屋,墙是用泥巴垒的,很矮,房顶结构看来很别致,用杂木棒、向日葵秆、麦秆编织而成,外面糊上泥,颇像南方的茅屋。
李大哥带我们围着村子绕了一圈,矮小的土坯房排成一排,每家门口种着几颗白杨树和槐树,周围是队里的庄稼地。这里属淮北平原,放眼眺望,一马平川,火红的太阳灸灼着每一个角落,丝毫也不比南方的日头逊色。夕阳从远方的村庄后落下,家家屋顶冒出缕缕炊烟。因为没有山坡,没有树林,没有高大的建筑,也就没有荫凉,夏日的傍晚显得比南方还热。入夜,我们和村里的男人们都睡在村口的打麦场,老少爷们都将裤叉挂在树上,光着身子睡觉,看来,北方人比南方人还会乘凉。
第二天,我们在李为相家里架起两块石头,放上个大陶钵,用牛羊油和烧碱开始了土法制皂。熬了十几个小时,油和水总是不能相融,我和为贵汗流浃背。其实小样试验我在长沙做过,无非是油和烧碱进行皂化反应,然后加入填充料。牛羊油和固体烧碱是制皂极好的原料,可偏偏就是做不成。李大哥站在旁边也干着急,赶紧拉起风箱灶给我们煮小米粥喝。我们一边喝粥,一边听李大哥讲朝鲜战争的故事。有一次,他们部队被美国兵包围,苦战了两天一夜,终于胜利突围。我苦笑着对李大哥说:“如果肥皂做不出来,我和为贵就打道回府;如果肥皂厂能生产,是您思想工作做得好,我们请您当肥皂厂的政委。”
经过反复试验,调整配料的比例以后,肥皂终于制成了。我们三人一起边吃早钣,一边商量下一步工作。为贵建议用烧饭锅先做上一锅,给全村每家送上一小块。另外我们还得给肥皂起个“名号”,李为相建议叫“贫农牌”,为贵说叫“公社牌”好。商量来商量去,都觉得不妥。我突然想起毛主席的“五七”指示里提到“亦工亦农”,我们是农民办工厂,肥皂就取名“五七牌”吧。只是肥皂太少,村里每家分不到一块。李大哥建议,肥皂不够,就多加点水。这倒是个好主意,于是我们给每家送去一块像牛皮糖一样的“五七牌”肥皂。
第二天傍晚,村子里的孩子们在水渠对面大声问我和为贵:“喂!光脚鸭子,你们的肥皂为什么叫‘五七牌’?”淮北人穷,但一般怎么都得穿双鞋,看到我们老是赤着脚,觉得特别,所以有时叫我们光脚鸭子。“小家伙,这还不懂,你们连毛主席的‘五七’指示都不知道?”“‘五七牌’的意思谁还不懂,就是每块肥皂只能洗五到七分钟!”一位小孩俏皮地说。
不管怎样,“五七”牌肥皂终于诞生了。
窝窝头我爱吃
为了正式投产,我和为贵准备去蚌埠采购一些原料,单程有110多华里。为了节约开支,我俩决定步行。我们走的是一条简易公路,当地叫“晴通雨阻”公路,这条窄窄的公路上稀稀落落地跑着几辆汽车和胶轮车。淮北平原虽然平坦,却没有钱修路,公路未铺砂石,晴天尘土飞扬,雨天满地泥泞,就像沼泽地一样。
我和为贵将解放鞋背在背上,光着脚赶路, 一图凉快,二图省鞋。开始,我们边走边欣赏平原的风光,不觉得累;而我们赤着脚赶路倒招来了不少好奇的眼光。走到七八十里地时,腿就酸痛起来。快到蚌埠已经很晚了,干脆在马路边草地上躺下来休息。一觉醒来,天已大亮,脸上和脚上满是蚊子咬的疙瘩。穿上鞋,在路边池塘里洗了个脸,拍打净满身的尘土就进了城。买好原料,赶紧去买回头车票。恰好那天天气好,车站挂出了“晴通雨阻”线的售票牌。买完票,口袋里只剩下了两分钱,肚子饿得咕咕叫。两分钱只好买一条菜瓜,为贵掂量了一下,逢中分开,每人一半。虽说是随手分开,在我心中的天平上两块菜瓜重量绝对是相等的。
回到村里,生产队腾出间房子,“五七”厂挂牌开张了。我们先用铁锅熬制好肥皂,像做豆腐一样倒在一个四面能拆开的木箱中,冷却后用钢丝切成块,然后用模具给每块肥皂压上“五七牌”大印,肥皂正式出厂了。
村里人轮番来参观“五七”厂,三十来岁的大嫂们全都光着膀子,两个奶子一甩一甩的,赤膊走到我们面前和我们聊天。初起我们很不自在,后来细想起来,他们和我们光脚走路一样,图的是凉快。
李为相的工作是担水、烧火、还管煮飯。烧火用的是省柴的风箱灶。风箱一拉起就腾起火苗,一停火焰就下去了,这样可以节省柴禾。经过反复琢磨,肥皂质量倒还不错,拉到集市上去卖,很快销售一空。小肥皂厂开始赚钱了。那一天我们为李为相添置了一张床,一张桌子、几张凳子。李为相还特意请队长、会计吃了顿飯,商议结果是这个厂由生产队来办,我们拿工资,于是皆大欢喜。
工厂越办越红火,来订货的人也不少,不到一个月,赚了几百元钱。队上给每家发了两条肥皂、两块钱,剩下的钱全部买了原料准备大干。队长跑来为我们打气,他说:“小周,你别回去了,在村里跟我们一起干吧,我们全村都是贫下中农,现在是我们贫下中农说了算。不过你们吃惯了南方的大米飯,这儿的窝窝头你吃得下吗?”“好,干就干,只要能当贫农,窝窝头我爱吃。
何处是归途
那天早晨,李大哥刚好将缸担滿,准备开工。突然闯进来一伙带红袖章拿长枪的人,自称是“马店贫下中农造反军”。有个领头的高个子宣称,肥皂厂是地下黑工厂,是搞投机倒把,全部财产要没收上交。李大哥怕我吃亏,一手揪住大个子,一手抓他背上的枪气呼呼地往外推,边推边喊: “肥皂厂是我办的,你把老子怎么办?他*的,你的枪口对准谁,朝鲜战场上美国鬼子的枪我都不怕,还怕你的吹火筒吗?”来人知道李大哥是打过美国鬼子的荣誉军人,而且有股连老婆都能打跑的傻劲,吓得向后退了几步。乡亲们趁机跑上来将我们团团围住,在老乡们的掩护下人溜出了大门。那伙造反派最后还是把我们苦心经营积累下来的全部家当,作为他们的战利品用大车拉走了,临走时还狠心砸了我们的锅灶,在门上贴了封条。
回到李为相家,三个人呆呆地坐在凳子上,一筹莫展,肥皂厂完蛋了,我们的希望成了肥皂泡,贫农没有当成,还差一点被当成投机倒把分子抓走……
真是祸不单行,这时为贵突然喊冷,紧接着哆嗦起来。我连忙将他扶到床上,给他盖上被子,他嘴唇发乌,牙齿叩得直响,脸上显出痛苦的神情。片刻又推开被子喊热,大汗淋漓。发烧过后有气无力地躺在床上。
病急乱投医,李为相在村东找到膀大腰园的李四卿,要他想法治。李四卿赶紧回绝:“俺大叔,您好糊涂,这些年靠队上分给我两担地瓜干能活得下去吗?在外地跑码头卖的药都是牛粪晒干碾碎做的,牛吃白草,百草都是药,我的药是什么病都治,什么病都治不好。”
村上派人骑车到镇上请来医生,医生诊断为疟疾,给了些药片。药片倒挺灵,服下后为贵再没有发作过。
已是11月底,家家都缝好棉袄准备过冬,冬天是这里最难熬的日子,吃的、烧的都成问题,去年大雪封锁了交通,家家户户锅内煮的、灶里烧的都是地瓜干。为了不加重乡亲们的负担,我们决定在寒潮到来之前赶紧离开,天一变想走也难了。村里人听说我们要走都来送行,我们含着泪告别了乡亲们。
几经周折,我们终于徒步走出了漫长的“晴通雨阻”公路,来到京广线上的滦河车站,搭上了南下的火车。这时寒风凛冽,下起鹅毛大雪,窗外已是白茫茫的一片。我穿着一件单薄的学生服,冷得紧缩着身子。回想起淮北平原几个月的生活竟像是一场梦,回去以后又该怎么办呢?
火车在原野上飞驰,离长沙愈来愈近了,我却是有家归不得,我真不知道,何处是归途……
(原文是我发表于2003年长沙市政协编的长沙文史:“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史料专辑”,编者对原文有些修改,现恢复原貌,供大家欣赏,原作基本记实,草根思者兄曾和我提及重庆《无声的群落》的编者想收集老知青的文章,此文可供他们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