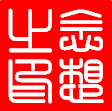知青琐忆------爬车
1977年上半年我们开始搞病退,翘妹子的病退材料先寄到长沙。她本人必须回长沙等待“复查”。这样一来,我们一家人分成了两起,她带着两个小儿子回了长沙,我带着大儿子留在乡里。
翘妹子来信说:“病退‘复查’还要等几个月的时间,家里一下增加了三个人吃饭,靠母亲和哥哥的那点口粮实在不够,要我想办法寄点粮票回长沙,而且还要快点寄来。
那天上午我挑了一百斤大米到铺口仓库换粮票,临走时我嘱咐大儿子,我换得粮票就回来,要他看好屋。莫玩远哒。我还把房门钥匙交给他,中午他自己就吃点冷饭算了。
大儿子那年六岁多了,很懂事听话。他操着那口标准金麦口音对我说;“你快克咯快回咯,我在外头孩(玩)到,我会瞅好屋的。”说完把钥匙藏在木柱子底下,还盖上一把草,生怕让人看见。
我见他那天真可爱的样子的好笑,我挑着米走了几步:“陈谷听话,爸爸买糖给你吃。”他小手摆不停:“欧欧欧!你快克!冒要紧的,我会瞅好屋的。”
十五里的马路,我挑着这担米连气都冒歇,就到了铺口仓库。仓库的老丰和小尹满口答应给我换票,因为我们这担米白花花的,比仓库那些米要漂亮得多。只是不能换省粮票,因为我冒带油,只能换成“划拨票”。他们说划拨票同粮票是一样的,在长沙照样可以购粮。只是要到县粮食局去兑票。可巧,现在正好有一辆运粮的汽车到县粮食局。我想这真是难得的机会?搭车到县粮食局兑得“划拨票”,就可以到县邮局将票寄到长沙,这样一天就可以将此事解决了吗?
于是,我将扁担箩筐寄放在小尹的房里,坐上了运粮的汽车,来到了县粮食局。我兑换得“划拨票”后直往县邮局走。
将一切都办好了,我总算放了心。我来到河街吃了几个“马打滚”,又包上两个给儿子。我路过西街饮食店,见里面有冰水买,于是,又买了一杯冰水。今天的天气实在太热,我也累了大半天。喝了这两杯冰水后一身舒服多了。
我起身准备走,突然望见那墙上挂的钟五点正了。我冒看错啵?我又问旁边一位带手表的人,没错!是五点正。我顿时脑壳一麻,我的天啊,五点钟我还在县城里,离我们金麦足足有四十里路,我今天只顾忙事,只估计到县城的时间,冒考虑返回的时间哒!
我儿子还望我回,我一想起在家的儿子,想起他向我挥手的那样子,心理就急了起来,我得赶快回去。我把“马打滚”放进裤口袋,大步大步跑了起来,一口气跑到了汽车站。
汽车站没有到铺口的汽车,怎么办?四十里路也不近啊。我又想起了儿子,我出门时冒拜托社员照应一下。我们是单家独屋。天黑了,怎么办?他在眼巴巴望我回啊。想起儿子那可爱的样子,我鼻子一酸,眼泪一下就流了出来。
来农村十二年了,我得出的结论是:知青流眼泪是没用的,知青不相信眼泪。我擦干了眼泪,迈步就跑!马拉松运动员一小时能跑几十里,我难道不行么?想起在家的儿子,我勇气来了,脚步越跑越快,一口气跑上了“老里坡”。
突然听见一阵车轮响。一辆拖拉机拖拖地开了。我连忙向他招手,可那位司机象冒看见我一样只往前开,我顾不了那么多了,一个箭步追上,两手求在车厢板上用力一撑。谁知用力过猛,一个跟头翻进了车厢,那车厢里是一层白白的石灰,弄得我一头发的白石灰,下身穿的是黑卡几布裤弄得白花花的。
我站在车厢上,拍了拍头上的石灰。那位司机回头望了望我也没做声,照样开他的车。我心里想不管这车开到那里,坐一段路是一段路,总比跑步要快些。拖拉机开到高桥地段,忽然向右一转弯。我连忙叫他停车。他象冒听见一样照样开他的车,我只能往下一跳。这一下跳得好,正跳在天髋边,身体重心一偏,麻扑一跤摔在田边。两手插在水田里,顿时,觉得小肚子一疼。被什么东西碰了一下。我吃力地把双手从田里抽出来。慢慢地爬了起来。我洗去手上的泥巴,抹去脸上的泥浆,摸了摸小肚子。还好,冒得事,我走了几步,冒伤哪里照样可以走。
于是,我又快步地走了起来,走了一段路,看看天色,太阳已经落山了。我还得抓紧时间,我又开始跑了起来,跟着跟着跑到了一段陡坡岭上。
我站在陡岭上望望后面,只见一辆汽车开来了,我心里想汽车比拖拉机开得快,要想爬上去必须在陡坡上爬,因为汽车要“挂挡”,车速会慢一些。果然不出我所料,汽车从我身边开过,我紧跟在后面追,大约追了十来米远,车速突然一慢,“挂挡”了。我加快步伐跑上前,两手求住车厢板。这一下我有经验了,我把右脚慢满跨上车厢板。斜过身子慢慢地跨进了车厢里。
司机可能还没有发现我,我看见车厢里有几块捆柴的条子,我估计这辆车可能是去拖柴火的,要是能到我们金麦该多好哟!
汽车比拖拉机要快得多,一下就过了“大弯”。紧接着又过了“茶树坳”。过了适哥和烟哥的屋边“官团下里”。车还在嚓嚓地向前开。我心里想这下可好了,一定是到我们金麦去拖柴的。可我高兴得太早,汽车开到一条便道口上突然一转,往“集中”大队方向开去。我只得求住车厢板,把脚慢慢地吊下来,滑了几步跳下了车。
我刚走出岔路口,见一辆拖拉机开过。我连忙追上去,一下就爬进了车厢,只可‘恨’这是辆云煤的拖拉机,可怜我上身穿的那件白衬衣,胸脯面前弄得墨黑一大块。那司机回头望望我笑了一下。我晓得,他是笑我这一身衣裤。一身的泥巴,白石灰,现在又加上一大块黑煤印。哎呀!我现在什么都不在乎了,我只希望车快点开,因为天色已经开始阴了下来。
拖来机开到铺口中学停了一下,我晓得这是进舒家那煤山的。我跳下了车,我路过铺口仓库,我没去拿扁担箩筐,我还得加快步子跑。因为离金麦还有15里路。我一口气跑到上铺口,走了一段路,又一口气跑上偏坡界。这偏坡上十里,大部分都是上岭。我跑几步,又走几步。总算到了冲耙界上。我望山下一看,金坑的社员正赶着牛回寨,这下我放心了。这里离家只有7里路左右,又全是下岭和平路。天虽然麻麻黑了,但估计到屋还是能看得见路的。
我又鼓起勇气把白衬衣一脱,捆在腰上,直往山下跑去。脚步已经到了”极点”。不停地跨动,一口气跑完下岭,又接着跑过了金坑生产队。我还是不停脚步,跑上了三拱桥看见了夏姐她们的屋了。
天已经黑下来了,蒙蒙地还能看见石板路。我跑过大队部,跑过木溪来到桂花树脚,我终于进寨了,看见了我的住屋。我跑到屋门前,没看见我儿子,我腿都发软了,我朝离我几丈远的那堆木桐上一望,有个小黑影在移动。我惊喜地喊了一声:“陈谷!”
“爸爸,你哟恩才回来哟?我坐在呆里老等老等啊!”他边说边朝我跑来。
我迎上去抱住他:“爸爸来迟噶,来迟噶”。说着眼泪不知不觉就流了下来。我把他紧紧抱在怀里,可怜我的知青儿。爸爸总算回来了。
那年月真可怜我们这些做知青父母的心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