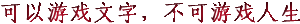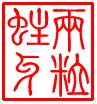这两年连续去了几趟华容。看到一些事,越想越搞不清白。
05年到了我们那个生产队,现在叫黄合村。从我们踏上进村的路算起,就没看到一个大人。即便是进到农家去,也只看到个大娃娃带着个小娃娃。许多家庭大门紧闭,铁将军把门。那次去时已经秋收完毕,田间地头已无劳动的人们。后来见着村支书打听,原来华容近几年来推行“劳务输出”。也就是说青壮年都进城打工去……。村里就剩了老头老太太和一些人们常说的留守儿童。饭桌上由于事先有准备,鸡鱼肉倒也丰盛。可我们提出想吃个青菜,农村好客的主人却拿不出几棵青菜待客。
今年4月我又去了三郎堰,特意去寻了趟菜市场。那菜市场里鸡和蛋杳无踪影,为数不多的鱼档,几条小鲫鱼在那水里翻着鱼肚,一打听价格,比长沙都贵出好多。只有出门的地方一个提蓝卖水芹菜的看着还水灵。
华容号称鱼米之乡,可鱼米之乡的农村没有菜吃谁信。可你细细寻思就会觉得这事也变的不奇怪了。不奇怪的原因就是那“劳务输出”上。
这几年电视、报纸等媒体上多讲关心农村的留守儿童。我就不懂了,那些出门打工的父母,狠心丢下年幼的孩子在家,怎么能安心工作。今年六月份,妹妹到隆回去旅游,回来讲旅游途中的所见所闻。她们入住的那个山村,极好的公路修到村口,可整个村里,只见了7个人,包括了教书的先生,背在背上的娃娃。更有的孩子自己还什么都不懂呢,还正是读书的年龄。就需要充当大人的角色,做饭带孩子,料理家务了。他们的父母顺着那条修得极好的公路走到山外“劳务输出”去了。
我们这帮城里人,家家都有打工的,还有许多“高级打工仔”,收入肯定超过那些“劳务输出”者。有谁看过靠打工发财的,靠“劳务输出”能富了一方水土的。
丢下那方土地,丢下老人和孩子任他们在家享受孤独和寂寞。为什么不能留在农村发展农村养殖业,不能留在农村发展农产品的深加工。
大量的农村人口流入城市,给城市带来了繁荣和发展。也给城市带来了负担和压力。那紧张的就业岗位,大量的失业青少年,给社会带来多少不安定因素。
那日我到解放四村见到一个推单车卖菜的,旁边买菜的似乎和他很熟。仔细听来那卖菜的汉子就是住在大椿桥的,买菜的是他家的邻居。我奇怪大椿桥还有菜园子吗?那卖菜的告诉我:
“原工作单位破了产,自己再找工作也难。没有一技之长又不甘心在家整天摸麻将,就到郊区包了4分地,一年交400元租金。今天第一天来卖菜。”
我问:“郊区有地可包?”
“都到城里做事哒。那些地长好深的草。”
我为那人再创业的精神感动着,在他那里买下了一大堆菜,不管能不能吃得完。一方面是城市里的失业人员,一方面是农村人口涌入城市造成的土地荒芜。
也许我是想得太多了……。打住、打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