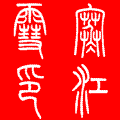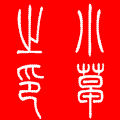我在安乡98年那场特大洪水中的经历
一九九八年八月七日,是一个永远载入安乡史册的日子。这天下午六点多钟,安乡安造大垸溃决,拉开了震惊全国的一场波澜壮阔的抗洪抢险序幕。九年过去了,当时的那种悲惨情景和那些惊心动魄的抢险经历仍在我脑子里挥之不去、刻骨铭心,那是我一生中最难忘的一段时光。
那天下午,安乡高洪压境,各地险情层出不穷,到处告急。其时,我担任指挥部工程科负责人。我接到城关交通闸(长沙班码头)出险的报告后,下午三点赶来出险地点,组织人员除险后,已是下午五点。因为我是专门负责指导处理险情的,顺便就给城关修防会主任和工程股长去电话,问还有不有需要我去解决的问题,并嘱咐二位一定要在现场巡视,不要放过任何出险苗头。当时,那位工程股长就在溃决险情现场,他们均向我作了平安无事的汇报。
我离开城关回到指挥部。刚吃完晚饭,正准备填写今天的巡查记录。忽报城关出现重大险情,险情就是命令!我立马驱车赶到出事地方。为时已晚!眼见滚滚黄流正把安乡棉纺厂大堤撕开一道四、五十米宽的口子,洪水以八、九米高的落差居高临下翻滚进来。堤下五十米开远的地方,一股碰到厂工人宿舍房后升起的水躍足足有两层楼高。灾祸来临,工人们有的穿短裤,有的抱着电视,有的拖着老人小孩,拼命往高处逃生,厂区一片漆黑,只听见咆哮的水声音和慌乱人们的叫喊声混成一片。我忙命令几辆小车打开车灯,给逃生的人们送去光亮。几个县指挥部的领导找我们综合了一下意见,感到受条件限制,这样的局面已无法抢救。最终大垸溃决。一道防线失守,决定找二线干堤救护,力图把损失降到最小程度。我们分头查看情况,发现棉纺厂小垸已冲跨,洪水像猛兽一样大量涌进书院洲哑河,然后向城关和安障南北两头分泄而下。
后来我了解的情况是这样的:下午巡逻民工发现棉纺厂靠堤的女洗澡堂内有河水漏出来,城关修防会工程股长带上一个工程员来处理,从一根已废的水管内发现流水,立即叫人挖水管找水的来源。其实,此时已发现水管旁有漏水带沙现象就是管涌(俗话沙眼),如果该股长稍有抢护知识,就应马上组织用沙卵压沙眼办法处理,而且要做大险报指挥所,组织大批劳力来救护。由于该人反应迟钝,没有看到问题的严重,等到把水管挖开并取出(取出是大错)时,涌水加大并大量带沙。此时如果压沙眼器材多也不会出大问题,等到事态严重,才猛地想起运沙卵,但为时已晚……。如果下午在我问他们有不有事时把我留下,我也可担保绝对可抢住,因为我处理这样的问题比他们有经验。事后,我反复问他们为什么不做大事来报告,他们说以为没大问题。就这么一次小小的失误,酿成了建国以来安乡的惊天大祸,我懊悔不已!设想了好多“如果”。因为我刚调过去才几个月,根本不知道还有这样马虎的下级,没想到他们那些汛前的信誓旦旦的“军令状”都是空话;那些不懂业务还在岗位上装腔作势、得到领导赏识的人,知不知道灾祸齐天而反省自己?!一切过去了之后,除撤职一名党委书记和一名管水利的党委委员外(因书记是干部的财富,不久又官复原职),一切又恢复了原来的样子。
再回到溃垸 当晚,凌晨二点,桃源、常德、澧县、汉寿、临澧等县支援大军赶到。我带着桃源几百人趟着齐腰的水,背着土袋,向棉纺厂摸去。因为水深,队伍无法再前进而折回安乡大桥边。我旋即驱车往安乡县城至黄山头方向的公路赶,企图把人从那边调过去。老天!我一看,公路冲断,车辆无法前行。此时,铺天盖地的洪水冲破安障干堤汹涌着向北奔去。我立即把情况向县指挥部报告。这道口一撕开,却给安乡城关带来喘息机会。接着城关保卫战就开始了。
从安乡县检察院到安尤桃花村约八公里,县指决定调全县(包括支援县)8000---10000劳力投入战斗。八月八日上午十点,县指交给我任务:十二点就上人挑!为把任务基本均匀地分下去,我带一班工程员,一边走,一边看,一边估算,还一边统计,一路过去,一路分过来,基本把任务分均匀了;把测量、计算、统计、分配等工序在最短时间内完成,使领导和工程员们惊叹不已。
大队伍一到,看着上涨的河水终于被压到子堤脚下,县城保住了!我才松了口气。三天来,整个安造大垸就是一个战场,无异于解放军苦战孟良崮、自愿军苦战上甘岭。三天三夜只睡了三、四个小时的我,好想美美地睡上一觉!不料,一场更大的战斗在等着我。南线刚溃堤,北线又面临更大的告急!
紧靠安乡县的湖北公安县的黄金大垸(60---70万亩集雨面积)溃决!“长江之水天上来”。80亿立方米的长江水推进到安乡北线,高出我县地面7---10米的水头,压在我们头上!历史上,为保武汉,50年代建成了荆江分洪工程。在特大洪水袭来时,直接由中央指挥,派部队在固定有防护的地方炸开口子泄洪,途经我县安生、安昌、安宏,走南县入西洞庭湖;再经东洞庭湖岳阳城陵矶回到长江。但此次威胁我们的洪水,刚好在确保垸上面。水一但泻下来,不但县城全部要被淹没,还威胁丰、裕、康、武、成、德这个大垸,安乡得全部完蛋。于是,“北大堤保卫战”拉开了序幕。
由省里郑培民副省长总指挥、常德市钦时中副市长副总指挥,县长和水利局长带上我们参加;我仍是负责工程安排和抢险业务。省军区舟桥部队来了一个团。湖北黄金垸水位达海拔45米,我北堤仅43.5米,因此北大堤抢高到45.5米,挡水1.5米以上,由于年久失修,堤身百孔千疮,险情不断发生。部队在那里发挥巨大作用,他们以最快的速度搭好浮桥,从黄山头下用重车拖来泥土,提供了抢修子堤土源.在重大险情发生时都是他们冲锋在前;他们下入水中筑起人墙,爬到岸上抢背沙包,其情景与电影、电视上没有两样。险情处理上仍然是由我来指导;钦市长是搞水利出身,关键时刻他身先士卒,亲临指挥,很受我们敬佩。指挥部设在一条船上(长沙班轮船),有空调,有卫星电话。印象最深的是,钦市长住在我们隔壁,他和我们一同起早贪黑,摸爬滚打,他经常把好吃的慰劳品转给我们。白天在外,我们除吃饭能坐一会儿外,由于没人轮换,都是不能休息的。晚上,手机挂在床边,和衣躺下,铃一响,条件反射地弹起来,抓起手电,穿上水靴,走过晃荡的跳板,跑步前往出事地点。我的几个同事,皆因酷暑和过度劳累,身体经受不了而中途退出沙场。一个多月下来,我经受了生命的极限挑战,皮肤晒得油黑,人也瘦了一圈。经过一番“血战”,北大堤保住了!我们胜利凯旋。回到局里,干部戏称“安南”(联合国秘书长、黑人)回来了。那年给我一个全县少有的“二等功”。
溃决四天后才把大垸灌满,离溃决地远的乡镇,村民救上了大部家财,离溃口近的地方损失较大,基本没死人。18万亩良田的垸内一片汪洋,送食物和水的汽艇来往穿梭,14万灾民全都被赶到堤上。堤上搭满了棚,住满了人,政府送走了一部分老弱病残去澧县山区。晚上的堤岸上煤油灯光闪闪,唉叹的灾民夜深了都安不下心来休息,一派萧条。我曾深入他们当中看过。每天都有粮食和水分配,堤上热热的,臭臭的,蚊虫肆虐,拥挤的帐篷房,一家老小堆在一起,男人、小孩都是赤膊上身,个个晒得乌黑。男人们下水捞鱼,女人做饭,收拾衣被,不想事时,倒也安闲;只是问到今后怎么办,才显出一脸无奈,计算自己家庭损失时,大部女人会潸然泪下。翻垸后,鱼虾很多,在倒口处,有人一天搞上千斤以上;那时一、二元钱可任你提一袋走。天凉后,大人、小孩穿着花花绿绿,长袍短套的捐赠衣服,成为灾区特有的一道风景。
溃口期间,江泽民,李鹏等中央领导曾来灾区现场察看,号召灾民团结抗灾,鼓励人民灾后重建。
后来火热的堵口战役我没参加。冬季改口放水,抽水规划我都参加。年底,我带着工程员,用国家的投资,在与湖北交界的北大堤又扎实干了一个冬天,安乡北大堤最终成为了固若金汤的湖南屏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