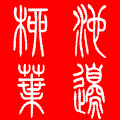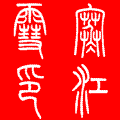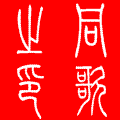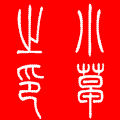我十分庆幸,在安乡的那段日子里,我遇到了一位好户主――严婶婶,回城快四十年了,可我总忘不了她和她们一家人对我们姊妹的关爱。
那年,我们从公社分配到正安大队11生产队,队长将我们姊妹带到了她的家里。我们第一次知道安乡盖的棉被有十多斤重,可我们只带了一床六斤的被子。运气不错,她丈夫是生产队的副队长,还是弾棉花的好手。搜尽了家中仅存的棉花,给我们弾了一床十二斤的又宽又大的新棉被,真是暖在身上更暖在心里。这床棉被一直陪伴我度过了在安乡的六个冬天。
那些年,在安乡能餐餐吃猪油炒菜那真是福气,这又让我们摊上了。过年她家杀了一头大肥猪,煎了一缸猪油足有五十来斤,看我们刚从城里来,总怕我们吃不好,餐餐猪油炒菜毫不吝啬。开始我们也觉得很正常,后来才知道,和我们在一个队的其他知青可没有我们幸运,吃过红锅子菜。特别是有的家里有好吃的,还背着知青留给自家的满儿子吃。而我们在严婶婶家里,从来没有亏待过我们,还总是要我们多吃点。
也不知道是不是不太适应安乡的水土,第一年双抢刚过,我的罗拐骨上长了一个疖子,安乡人叫“罗炎苍”〔音〕,真的是很痛。特别是躺了一会儿再起来,真是痛得钻心。后来用红膏药拖出的‘脓头’差不多有寸多长。为了减少我的痛,严婶婶每餐都把饭菜送到我的床边,还有她的小女儿,把她家杏子树上的杏子洗干净一盆盆放在我的床头。我就这样在她家过了一段‘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好日子。远离故乡的我,此刻感到了莫大的安慰,享受了她们一家给我的亲情般的温暖。
快四十年了,如今她老已近八十岁,儿女们有几个还在长沙打工,最调皮的小儿子从部队转业也在长沙工作,我们还经常有来往,彼此心中似乎都有一种牵挂,我想,这就是知青生涯中的情结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