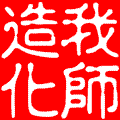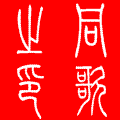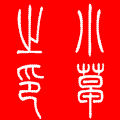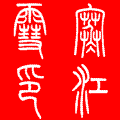原生态的文章《小余》在安知网发表以后,勾起了很多知青网友对这个几近被人遗忘的知青小妹的怀念。我的触痛很深:这不但是由于我对于邻大队的这对知青兄妹比较了解,而且文革以前我的弟弟和妹妹就已经和他们家的兄弟姊妹来往频繁了,因而对于他们家庭身世比较了解的缘故。
几天来,一种悲情和责任的驱使,我通过弯弯曲曲的途径,终于联系到了他们的家人,了解到了他们兄妹后续的故事和他们家人现在的概况。他们的父母已经不在人世,而且原先我隐约听到的余泽野也已经去了的传闻得到了证实。
余泽野和余依群兄妹下面还有两个弟弟现在长沙,泽野的唯一女儿余涵芬在长沙某医院当护士,老婆已经改嫁。他们的大弟弟接到我的电话,听完了我的身份介绍和电话来意之后,显得非常激动;他似乎又听到了他哥哥姐姐久违的声音,唤起了他对于逝去的同胞姊妹的深深的怀念。
“小余”一家文革以前就深受磨难:父亲开始在省供销社工作,后由于历史问题受到不公正对待遣返到湘西通道县,母亲没有工作,兄弟姊妹四人全靠母亲没日没夜地劳累和亲人的接济度日。我的弟妹告诉我,那时他家的状况就目不忍睹。
69年知青下乡,余泽野作为附中初81班的学生随学校到安乡。妹妹余依群小学毕业,本不在“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的对象之列。但是,在那个风声鹤淚的年代,她母亲哪里有敢不积极响应号召的胆子呢?再者,留在城里吃什么呢?于是,这个未成年的妹妹就跟着哥哥也来到了广阔天地。
兄妹俩人落在杜家3队,我去过他们的知青屋,那是比我们的知青屋要简陋得多的茅蜡烛三面体,堂屋朝南的一面没“墙”,也算能避风雨。长期的政治上的倍受歧视和家里的惨状,以及对于跟随自己而来的妹妹的责任心的压力,致使哥哥沉默寡言,鲜与他人来往;特别在70年代初父亲去世后,这种状况更甚,当时在杜家的知青中他是最“霉”的一个。妹妹“小余”到底年幼无邪,显得比哥哥开朗得多,特别是到大队代销店站柜台以后,逢人有说有笑;正如原生态所描叙的一样,对于来往的知青她尤其热情。沙阳知青去县城总要经过她那里落脚,她总是亲人一样迎接我们。
1973年,小余无声无息地病重去世了,我们当时很震惊!也就刚刚20岁,正是豆蔻年华,怎么说走就走了呢?30多年来,每每和杜家知青谈起小余,大家总是唏嘘不已;今天回忆起她的音容笑貌,还有说不尽的伤痛。
由于出身在一个不幸的家庭,她从小就没有享受过童年的欢乐和应有的幸福;在下乡期间过早去世,还没有来得及回报父母的养育之恩;这对于她母亲,当时又是多么大的打击。她一生中得到的最多的关爱,可能就来自于和她命运相同的知青朋友。在她病重和去世期间,杜家4队知青吕良亚奔走于安乡与长沙之间,一直陪伴招抚她。说到这些往事,她弟弟至今没有忘记。
妹妹死后,哥哥余泽野被照顾招工到挖泥船队,这时他已发现体力不支,经检查得的是血吸虫病。在挖泥船队的一年多时间里,他有过短暂的欢乐,也结了婚,生有一女儿,但据说后来婚姻并不美满。此后,他通过关系调到长纺食堂,再后来又得了心脏病。到1994年他病逝之前,已经骨瘦如柴,肤色腊黄了。
安康知青中的凄凉故事和不幸的结局,还有超过他们俩兄妹的么?我几天来寝食难安:摇曳在杜家3队沟边的那个破败的知青小屋、杜家代销店那张活泼热情的小余的笑脸、穿着一件破棉衣,总是心事沉沉的那个余泽野的记忆中的形象,历历出现在眼前。一个家庭和一对知青兄妹的苦难延续了这么多年;我们乘一条船去安乡的校友和伙伴,就这样双双离开我们,实在是不堪目睹和回忆!我想起了冯骥才在他的《100个人的10年》一书中记录的那些文革10年中的典型人物的悲惨命运,余氏兄妹的命运与他们雷同。
如今,我们这些生者在积极筹备知青下乡40周年活动,可惜小余兄妹已不能参加其中了!如果他们还有在天之灵,一定还在注视着我们的安知网,一定会感谢我们对他们没有忘却的纪念。
愿小余兄妹的魂灵在天国里安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