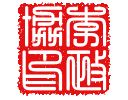作为黄克诚的同乡同宗,我对他一直怀着特殊的感情,特别是他那实事求是、追求真理的思想品质,刚正不阿、坚持真理的铮铮铁骨,历尽坎坷、百折不挠的坚定信念,严于律已、艰苦朴素的公仆形象,深谋远虑、大公无私的博大胸怀,使我产生深深的敬意。
1981年10月,我幸运地见到了仰慕已久的黄克诚大将,受到了他老人家亲切热情的接待,进行了六次交谈。黄老高开我们十多年了,但我在乡在京所见所闻关于他的桩桩往事,不但没有淡忘,反而放射出越来越夺目的光彩。
如此“将军府”
我们拜访黄克诚将军的时候,正在住院的黄老身体很虚弱,医院不让他外出,以免受风寒。他为了陪我们吃顿饭,硬是破例离开医院,同我们一起回到了家中。
当车子驶进王府井附近一家小院子的时候,我怎么也不相信,这就是共和国开国大将的“将军府”。我们心目中的“将军府”,应该有一个又高又大又威武的大门,可黄老的家门是又低又小又陈旧,屋上的木板有的都朽得掉下来了。工作人员介绍说,这房子冬天透风,夏天漏雨。漏雨的地方正好对着黄老的床,他就在床上放了一个接水的脸盆。每当晚上黄老入睡之后,往往被附近消防站的汽车报警器吵醒。
一位劳苦功高的开国大将,又年迈、体弱多病之际,住的竟是这样的房子,有关管理部门为什么不管?工作人员说:“不是不管,是黄老总不让人管。管理部门曾多次劝黄老搬迁或翻修,但黄老就是不同意。他说,我们的国家还很穷,群众住房更困难,很多家庭的几代人同住一房。比起他们来,我的房子不知要好多少倍!管理部门的同志说:这里太吵了,给您换个安静的环境吧。黄老说:换别人来住,不是一样吵吗?
后来因为从房顶上掉下一块朽木板,正好砸在黄老床边,差点伤着正在休息的黄老,他才同意翻修一下。但一听说这次翻修要用几万元钱,他又不同意了;只允许哪里坏了哪里修一下,只要下雨、化雪不漏就行了。
用漏雨的问题算是暂时解决了,但漏风的问题却越来越严重,年轻入坐在他家都冻得直跺脚,何况他又年迈多病,服务部门考虑到他家门前有地下热力管道经过,计划花3万元把他家改装成由热力管道供给暧气。水暖工掘开了管道周围的土,运来了暖气设备,被黄老发现后,又制止了。
关于小车的家规
黄老六次接见我们,都是他的秘书与司机用他的小轿车接送我们到医院细谈的。
秘书丛树品说:黄老对家乡来人这么热情要算第一次了。别的不说,光是在车子的使用上,“政策放宽”得实在可以了。黄老曾对家人严格规定:“小车是国家配给我办公用的,不能私用。”多年来,子女们一直自觉遵守这一家规。家乡来客也不例外。有一次,黄老老家的侄子、侄女带着孩子们进京看望他,受到热情接待,并乘班车游览了很多京城名胜古迹。亲人们最后想游览八达岭,而八达岭没有班车,挤公共汽车也不方便。黄老身边工作人员问:是否动用一下小车?黄老果断地回答:“不行,可以坐火车,车费由我负担。”
我们听了丛秘书的介绍,感到不好意思起来,丛秘书似乎看透了我们的心思,连忙解释说:“黄老历来是公私分明。你们征集党史资料,是全党当前一大公事,理应提供方便。”他又给我们讲起了黄老小儿子结婚时用自行车接新娘的故事。
当时社会上盛行婚嫁讲排场、摆阔气之风,无论大小城市,结婚,都是一长溜小车子。现在黄老的小儿子结婚,是否可以用一下小车呢?面对工作人员的请求,黄老严肃地说:“这个‘戒’不能开。年纪轻轻的,坐公共汽车,骑自行车,都可以来嘛,为什么要开着小车抖威风?”于是,小儿子真的用自行车把新娘接回来,全家人与工作人员一起吃顿饭,就算把一桩喜事办完了。
司机王秀全还告诉我们:“我给黄老开车已十年,只一次自作主张要送他的掌上明珠--小孙子上学,却碰了壁。那天清晨,下着大雨,雷鸣电闪,我看到黄老的孙子黄健撑着雨伞,卷起裤腿去上学,心理不忍,便自作主张要送一趟,却被黄夫人阻住了:“不能破了这个家规。”她边说边撑伞,把孙子送到了公共汽车站。”
一篇新闻稿的命运
在向黄老了解党史资料的过程中,黄老对人对事对历史的实是求是、严肃认真的态度,使我很受感动,就写了一篇题为《黄克诚同志指出,要为后人留下真实史料》的新闻稿,寄给了《人民日报》。
《人民日报》编辑王瑾同志收到这篇新闻稿后非常高兴,如获至宝。他在电话中对我说:“彭、黄、张、周平反以后,彭、张、周都进行了大量的宣传,唯独黄没有宣传过。今天你寄来的稿子,真是雪中运炭。”他把小样编好铅印出来后,寄了一份给黄老。不料黄老秘书王又新的回答是:“最好不要用。黄老本人曾多次说过,不要宣传他自己。”
于是,王瑾又怀着遗憾的心情,把此新闻稿小样寄给了我。
我收到这篇小样后,当即交给了县委书记。县委书记说:“他《人民日报》编印好了小样,却因黄老秘书一句话就不敢发表了,我们拿到《湖南日报》去发表。你到长沙去找省政协副主席兼统战部长谷子元同志,请他出面牵线搭桥。因为谷老最了解、最敬重黄老,肯定会势心的。”
果然不出所料,我赶到长沙谷老家里,已是大年三十了。谷老热情地接待了我,并深有感触地说:“黄老真是一位世上少有的好同志啊,但感他老人家活到一百岁。《人民日报》既然热情地编印了小样,发表就是了,何必征求黄老的意见?黄老这人心理只有同志,只有党的事业,唯独没有他自己。他怎么愿意宣传自己呢?”接着,他陪我坐着小车去了湖南日报社,找到了汪总编,汪总听了我们的介绍以后,也遗憾地说:“实在对不起谷老一片心,他《人民日报》不敢用,我《湖南日报》也不敢用了。这一瓢冷水把我热乎乎地心浇冷了,但谷老还是不灰心,硬是找到当时管文教卫的省委副书记焦林义同志,最后在《湖南宣传》杂志上发表。
另一副“眼镜”
在1981年搜集党史资料那次拜访中,我曾问过黄老:在湘南暴动中,湘南特委指示要大烧大杀,时任红色警卫团党代表兼参谋长的您,为什么能与在井冈山的毛泽东,英雄所见略同,力持异议,使水兴城大部分房屋保存下来,避免了物极必反的恶果?在第三次反“围剿”前后的大规模肃反中,时任师政委的您,为什么敢于违抗命令,把所谓“AB团”分子藏进山洞?1959年的反右,矛头本来是对着彭德怀的,而您是被搬上庐山的“救兵”,是毛泽东争取反戈一击的现象,您却不愿落井下石,反而替彭德怀讲话,导致自己身处长达近20年的险恶逆境,。20年后,毛泽东已去世了,在纠左声浪中,而您却以党和人民的根本利益为重,挺身而出,维护毛泽东及毛泽东思想。历史充分证明,您从不顾个人安危替彭德怀讲话,到不计个人思想为毛泽东说话,是难能可贵的,是一种什么力量驱使您这么做呢?
黄老明确回答说:“是真理的力量。”
“那为什么当时有人看不到真理,而您能独具慧眼看到,并能坚定不移、义无返顾地为之奋斗呢?”
黄老风趣地说:“因为我有副党和人民给的眼镜啊,我所说的眼镜不是指我佩戴的这一副,而是指另一副无形的眼镜。有形眼镜只能解决观察事物表象问题,无形眼镜才能解决观察事物本质问题。”
看到黄老佩戴的眼镜,听到黄老所说的:“无表的眼镜”,使我想起了很多往事:黄老的眼镜与他自幼勤奋好学分不开。从蒙馆、经馆、“凛溪书院”,到县城高等小学,他的学习进展比一般人快一倍以上。当时蒙馆、经馆要四年学完的《四书》、《五经》等,他两年就读完了。当时高等小学三年课程,他一年半就读完了,接着又考上了衡阳省立第三师范。由于他刻苦读书而又生活困难,营养不良,早在十来岁时就戴上了近视眼镜。从此以后,不管是放学回家下地干活,还是在部队行军打仗,他再也离不开这副眼镜了。
读书损害了他的视力,知识却大大增强了他观察事物的能力。1945年他提出建立东北根据地的建议时,陈毅就说过:“别看你们黄师长戴着近视眼镜,他的眼睛看得可远了,是千里眼。”
黄老却说:“我哪有什么千里眼,我所以有点观察力,主要得益于勤读书,勤实践,勤思考,借助于另一副无形的眼镜。”
黄老读马列的书,始于1922年考入衡阳三师之后。三师早在1921年就成立了“新书贩卖部”,设立了毛泽东创办的长沙“新文化书社”的分社。自幼酷爱读书的黄克诚,如饥似渴地阅读者《共产主义ABC》、《新青年》、《向导》、《每月评论》等各种革命书刊。他除了自己孜孜不倦的读书外,还提议成立了“永兴旅衡学友互助社”,交流读书体会。互助社成员凑钱购了一批国内外进步书刊,他担任图书管理员。这时他认真阅读了达尔文、克鲁泡特金、马克思、恩格斯、布哈林等人的著述。特别是《共产党宣言》,他读得格外认真。此后,他又想方设法找来了各种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书刊,认真地阅读、思考,思想上产生了质的飞跃。
黄老说:“我的这个决心不是轻易下的,而是认真、郑重、长期考虑的结果,因而是不可动摇的。”黄老引用毛泽东的话对我们说:我们的眼力不够,应借助于马克思主义的望远镜和显微镜,这就是我们每个共产党员必备的无形眼镜。只有坚持勤读书、勤实践、勤思考,才能用好这副无形的眼镜。1986年,在黄克诚的追悼大会上,杨尚昆致悼词时说:“黄克诚同志具有共产党人的优秀品德。他胸怀坦荡,顾全大局,为了党的整体利益,总是不惜牺性个人和局部的利益。他不居功,不擅权,全心全意为人民的利益而奋斗。……他模范地遵守党的纪律,艰苦朴素,廉洁奉公,处处以身作则,坚持党的优良传统,并严格教育子女和身边的工作人员,堪称共产党人的楷模。”这个评价准确地道出了黄老的高尚品质,表达了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对黄老的崇敬心情。
1981年10月,我幸运地见到了仰慕已久的黄克诚大将,受到了他老人家亲切热情的接待,进行了六次交谈。黄老高开我们十多年了,但我在乡在京所见所闻关于他的桩桩往事,不但没有淡忘,反而放射出越来越夺目的光彩。
如此“将军府”
我们拜访黄克诚将军的时候,正在住院的黄老身体很虚弱,医院不让他外出,以免受风寒。他为了陪我们吃顿饭,硬是破例离开医院,同我们一起回到了家中。
当车子驶进王府井附近一家小院子的时候,我怎么也不相信,这就是共和国开国大将的“将军府”。我们心目中的“将军府”,应该有一个又高又大又威武的大门,可黄老的家门是又低又小又陈旧,屋上的木板有的都朽得掉下来了。工作人员介绍说,这房子冬天透风,夏天漏雨。漏雨的地方正好对着黄老的床,他就在床上放了一个接水的脸盆。每当晚上黄老入睡之后,往往被附近消防站的汽车报警器吵醒。
一位劳苦功高的开国大将,又年迈、体弱多病之际,住的竟是这样的房子,有关管理部门为什么不管?工作人员说:“不是不管,是黄老总不让人管。管理部门曾多次劝黄老搬迁或翻修,但黄老就是不同意。他说,我们的国家还很穷,群众住房更困难,很多家庭的几代人同住一房。比起他们来,我的房子不知要好多少倍!管理部门的同志说:这里太吵了,给您换个安静的环境吧。黄老说:换别人来住,不是一样吵吗?
后来因为从房顶上掉下一块朽木板,正好砸在黄老床边,差点伤着正在休息的黄老,他才同意翻修一下。但一听说这次翻修要用几万元钱,他又不同意了;只允许哪里坏了哪里修一下,只要下雨、化雪不漏就行了。
用漏雨的问题算是暂时解决了,但漏风的问题却越来越严重,年轻入坐在他家都冻得直跺脚,何况他又年迈多病,服务部门考虑到他家门前有地下热力管道经过,计划花3万元把他家改装成由热力管道供给暧气。水暖工掘开了管道周围的土,运来了暖气设备,被黄老发现后,又制止了。
关于小车的家规
黄老六次接见我们,都是他的秘书与司机用他的小轿车接送我们到医院细谈的。
秘书丛树品说:黄老对家乡来人这么热情要算第一次了。别的不说,光是在车子的使用上,“政策放宽”得实在可以了。黄老曾对家人严格规定:“小车是国家配给我办公用的,不能私用。”多年来,子女们一直自觉遵守这一家规。家乡来客也不例外。有一次,黄老老家的侄子、侄女带着孩子们进京看望他,受到热情接待,并乘班车游览了很多京城名胜古迹。亲人们最后想游览八达岭,而八达岭没有班车,挤公共汽车也不方便。黄老身边工作人员问:是否动用一下小车?黄老果断地回答:“不行,可以坐火车,车费由我负担。”
我们听了丛秘书的介绍,感到不好意思起来,丛秘书似乎看透了我们的心思,连忙解释说:“黄老历来是公私分明。你们征集党史资料,是全党当前一大公事,理应提供方便。”他又给我们讲起了黄老小儿子结婚时用自行车接新娘的故事。
当时社会上盛行婚嫁讲排场、摆阔气之风,无论大小城市,结婚,都是一长溜小车子。现在黄老的小儿子结婚,是否可以用一下小车呢?面对工作人员的请求,黄老严肃地说:“这个‘戒’不能开。年纪轻轻的,坐公共汽车,骑自行车,都可以来嘛,为什么要开着小车抖威风?”于是,小儿子真的用自行车把新娘接回来,全家人与工作人员一起吃顿饭,就算把一桩喜事办完了。
司机王秀全还告诉我们:“我给黄老开车已十年,只一次自作主张要送他的掌上明珠--小孙子上学,却碰了壁。那天清晨,下着大雨,雷鸣电闪,我看到黄老的孙子黄健撑着雨伞,卷起裤腿去上学,心理不忍,便自作主张要送一趟,却被黄夫人阻住了:“不能破了这个家规。”她边说边撑伞,把孙子送到了公共汽车站。”
一篇新闻稿的命运
在向黄老了解党史资料的过程中,黄老对人对事对历史的实是求是、严肃认真的态度,使我很受感动,就写了一篇题为《黄克诚同志指出,要为后人留下真实史料》的新闻稿,寄给了《人民日报》。
《人民日报》编辑王瑾同志收到这篇新闻稿后非常高兴,如获至宝。他在电话中对我说:“彭、黄、张、周平反以后,彭、张、周都进行了大量的宣传,唯独黄没有宣传过。今天你寄来的稿子,真是雪中运炭。”他把小样编好铅印出来后,寄了一份给黄老。不料黄老秘书王又新的回答是:“最好不要用。黄老本人曾多次说过,不要宣传他自己。”
于是,王瑾又怀着遗憾的心情,把此新闻稿小样寄给了我。
我收到这篇小样后,当即交给了县委书记。县委书记说:“他《人民日报》编印好了小样,却因黄老秘书一句话就不敢发表了,我们拿到《湖南日报》去发表。你到长沙去找省政协副主席兼统战部长谷子元同志,请他出面牵线搭桥。因为谷老最了解、最敬重黄老,肯定会势心的。”
果然不出所料,我赶到长沙谷老家里,已是大年三十了。谷老热情地接待了我,并深有感触地说:“黄老真是一位世上少有的好同志啊,但感他老人家活到一百岁。《人民日报》既然热情地编印了小样,发表就是了,何必征求黄老的意见?黄老这人心理只有同志,只有党的事业,唯独没有他自己。他怎么愿意宣传自己呢?”接着,他陪我坐着小车去了湖南日报社,找到了汪总编,汪总听了我们的介绍以后,也遗憾地说:“实在对不起谷老一片心,他《人民日报》不敢用,我《湖南日报》也不敢用了。这一瓢冷水把我热乎乎地心浇冷了,但谷老还是不灰心,硬是找到当时管文教卫的省委副书记焦林义同志,最后在《湖南宣传》杂志上发表。
另一副“眼镜”
在1981年搜集党史资料那次拜访中,我曾问过黄老:在湘南暴动中,湘南特委指示要大烧大杀,时任红色警卫团党代表兼参谋长的您,为什么能与在井冈山的毛泽东,英雄所见略同,力持异议,使水兴城大部分房屋保存下来,避免了物极必反的恶果?在第三次反“围剿”前后的大规模肃反中,时任师政委的您,为什么敢于违抗命令,把所谓“AB团”分子藏进山洞?1959年的反右,矛头本来是对着彭德怀的,而您是被搬上庐山的“救兵”,是毛泽东争取反戈一击的现象,您却不愿落井下石,反而替彭德怀讲话,导致自己身处长达近20年的险恶逆境,。20年后,毛泽东已去世了,在纠左声浪中,而您却以党和人民的根本利益为重,挺身而出,维护毛泽东及毛泽东思想。历史充分证明,您从不顾个人安危替彭德怀讲话,到不计个人思想为毛泽东说话,是难能可贵的,是一种什么力量驱使您这么做呢?
黄老明确回答说:“是真理的力量。”
“那为什么当时有人看不到真理,而您能独具慧眼看到,并能坚定不移、义无返顾地为之奋斗呢?”
黄老风趣地说:“因为我有副党和人民给的眼镜啊,我所说的眼镜不是指我佩戴的这一副,而是指另一副无形的眼镜。有形眼镜只能解决观察事物表象问题,无形眼镜才能解决观察事物本质问题。”
看到黄老佩戴的眼镜,听到黄老所说的:“无表的眼镜”,使我想起了很多往事:黄老的眼镜与他自幼勤奋好学分不开。从蒙馆、经馆、“凛溪书院”,到县城高等小学,他的学习进展比一般人快一倍以上。当时蒙馆、经馆要四年学完的《四书》、《五经》等,他两年就读完了。当时高等小学三年课程,他一年半就读完了,接着又考上了衡阳省立第三师范。由于他刻苦读书而又生活困难,营养不良,早在十来岁时就戴上了近视眼镜。从此以后,不管是放学回家下地干活,还是在部队行军打仗,他再也离不开这副眼镜了。
读书损害了他的视力,知识却大大增强了他观察事物的能力。1945年他提出建立东北根据地的建议时,陈毅就说过:“别看你们黄师长戴着近视眼镜,他的眼睛看得可远了,是千里眼。”
黄老却说:“我哪有什么千里眼,我所以有点观察力,主要得益于勤读书,勤实践,勤思考,借助于另一副无形的眼镜。”
黄老读马列的书,始于1922年考入衡阳三师之后。三师早在1921年就成立了“新书贩卖部”,设立了毛泽东创办的长沙“新文化书社”的分社。自幼酷爱读书的黄克诚,如饥似渴地阅读者《共产主义ABC》、《新青年》、《向导》、《每月评论》等各种革命书刊。他除了自己孜孜不倦的读书外,还提议成立了“永兴旅衡学友互助社”,交流读书体会。互助社成员凑钱购了一批国内外进步书刊,他担任图书管理员。这时他认真阅读了达尔文、克鲁泡特金、马克思、恩格斯、布哈林等人的著述。特别是《共产党宣言》,他读得格外认真。此后,他又想方设法找来了各种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书刊,认真地阅读、思考,思想上产生了质的飞跃。
黄老说:“我的这个决心不是轻易下的,而是认真、郑重、长期考虑的结果,因而是不可动摇的。”黄老引用毛泽东的话对我们说:我们的眼力不够,应借助于马克思主义的望远镜和显微镜,这就是我们每个共产党员必备的无形眼镜。只有坚持勤读书、勤实践、勤思考,才能用好这副无形的眼镜。1986年,在黄克诚的追悼大会上,杨尚昆致悼词时说:“黄克诚同志具有共产党人的优秀品德。他胸怀坦荡,顾全大局,为了党的整体利益,总是不惜牺性个人和局部的利益。他不居功,不擅权,全心全意为人民的利益而奋斗。……他模范地遵守党的纪律,艰苦朴素,廉洁奉公,处处以身作则,坚持党的优良传统,并严格教育子女和身边的工作人员,堪称共产党人的楷模。”这个评价准确地道出了黄老的高尚品质,表达了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对黄老的崇敬心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