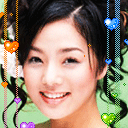今天(7月4日)的《扬子晚报》以《法国女音乐家南京开音乐会被嘈杂观众气哭》为题,配图报道了法国女音乐家布菲 女士在南京的这次难忘的记忆。
6月29日晚,在南京艺术学院音乐厅,活泼好动的孩子上蹿下跳,大呼小叫,手机铃声、说话声此起彼伏,面对这些并不高雅的景况,来自法国巴黎国立音乐学院的布菲教授情绪激动,她的眼眶里盈满了泪水,演出也被迫中断。一个法国著名教授,竟然在中国的音乐会上被气哭掉泪,闻所未闻!
据说,这些细节经常会发生在国内的高雅音乐会上,这似乎是一个无法解决的老话题,而国人早就见怪不怪。
不少看了那场演出的南艺音乐学院老师都对布菲的精湛演出留下了深刻印象。已跟随布菲学习三年钢琴的牛翔宇,目前就读于巴黎音乐师范学院,也是布菲中国音乐之旅的翻译。她告诉记者,布菲弹奏李斯特和舒曼的作品在法国可谓首屈一指,她任教的巴黎国立音乐学院也是全欧洲最好的音乐学院。
我不想说南京人素质如何如何,其实大家都明白,大多数国人估计都差不多吧。
我只想谈谈我“脸红”的原因。
首先,我为我是一名中国人脸红。
据说,布菲教授事后并没有指责南京的观众如何素质不高,只是感到不理解而已。多宽容的人呀,与之相比,我的脸更加红了。反观我们国人,在公共场合大声喧哗,大声吆喝,大声打招呼,大声接听手机,早已司空见惯,在声高气壮的氛围里尽情地显露着自己盲目的自豪感和浅薄的虚荣心。在文化层面,我们要融入国际社会,或者与国际接轨,看来还有一段路要走。
其次,我为我是一名大人脸红。
孩子是一张白纸,很多时候孩子身边的大人充当的是画师的角色,在有意无意间,我们把孩子塑造了出来。孩子其实就是我们的镜子,他们身上的毛病往往可以从我们这些大人身上找到渊源。
再次,我以我是文化人而脸红。我受过高等教育,我相信能够主动花钱去欣赏高雅音乐,除了极个别附庸风雅者之外,还是应该具有一定修养的人居多。但是,我们显然还没有把音乐厅和茶馆分清,没有把音乐家和艺人分清,没有把肉麻和有趣分清——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没文化”,顶多混了张文凭而已。
中华民族要在世界东方再次崛起,显然我们每个人要做的事情还很多。
真怕有的人连“脸红”的感觉也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