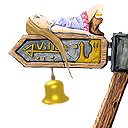难忘那年九月九
我的爷爷和父亲都不能幸免。事后听弟弟说,父亲被挂上“右派分子”的牌子,祖父也被挂上“反动文人,资本家”的牌子,治安指挥部的来人气势颇凶,而祖父却偏不服气,和他们顶撞起来:“你们莫神气,土改是二流子斗地主,等到地主斗得差不多了,就会轮到斗二流子了。”
在千里之外的湘南某县红云公社一个小山村,穷山僻野里的运动却更加野蛮,残酷。那天上午我送一担公粮到18里地外的允山区粮站,刚一回家,发现气氛不对,我唯一的财产—两只大樟木箱被贴上封条,上写“贫下中农封”,箱子里装的是我喜爱的一些文学书籍。眼前的情景使我十分愤怒,有谁能代表贫下中农封我的箱子?一气之下,我撕去了封条,想不到却惹来了一场横祸。
入夜,几个拿着鸟铳的机械民兵冲了进来,不由分说地把我捆了个严严实实。把一块用铁丝穿好的黑板挂在我的脖子上,上书“破坏三查一清的现行反革命分子xxx”几个大字,然后把我压赴批斗会会场。
会场设在门楼进口处的大队会议室,这也是我每天晚上给农民青年上课的夜校,没想到变成了我的批斗台。
会场四周挂了几盏煤油灯,台上书写着标语,台的两边站着一排揹枪的民兵,显得阴森、恐怖。我一进场,会场上就喊起了打倒我的口号,大队支部书记谭xx在台上拉长脖子,歇斯底里地吼叫着,一撮头发遮着前额,甩来甩去,使我想起了当年的希特勒。他首先宣布了我的罪行,他说我出生反动家庭,坚持反动立场,在此次中央文革发动的“三查一清”运动中,公然对抗贫下中农的革命行动,是货真价实的反革命。他说我这样做决不是偶然的,是有预谋的反革命行动。他还要我交代子虚乌有的反动组织的名称,成员名单,组织纲领,枪支弹药。
他是十分恨我的,因为67年9月在他指挥下的大队“贫下中农最高法院”用鸟铳杀了三个人,其中两人是富农,一个是道县修水库移民的外地贫农。我曾经背后讲过他是目无王法的土皇帝,他对此怀恨在心,此次趁机报复。在批斗台上,我又和他顶撞起来:“我是听毛主席的话,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不是反革命。你杀害贫农才是反革命”。
“还不老实!”民兵营长打了我一记耳光,将捆我的绳子愈勒愈紧,我的手也一阵阵钻心的痛,此是我第一次知道捆绑刑法的厉害,绳子渐渐地嵌入我皮肉之中。
我又用目光迅速扫了一下台下的乡亲们,不少人低着头,显然他们不忍看眼前的一幕,我的一些学生眼里都含着泪,我知道,在台上对我张牙舞爪的就只有那么几个坏东西。
一阵口号声中,我被悬空吊了起来,剧痛中我晕了过去。
……
昏迷中我恍惚又和我的夜校学生水养、送崽等一群年青活泼的小伙子在一起。为了赚钱给夜校买煤油,买课本,我们一起又在山上砍柴烧炭,他们在山上砍下杂木树,一根根放倒后,滑下来,我在下面接着,把它们拖到挖好的木炭窑边……当我们干得正欢,突然一声嚎叫,是一只凶狠的野猪向我直扑过来,我吓得拔腿就跑,可怎么也跑不动,我惊醒过来,吓出了一身冷汗。原来我已被关在生产队的粮仓中,我的两个手臂已觉麻木而且血肉模糊,双脚仍被绳子绑在粮仓的木柱子上。
第二天正逢赶闹子(集),我又被押送着参加了红旗公社的批斗会,首先是游街,然后是批斗。允山闹子(集)上,名目繁多的阶级敌人挂着形形色色的闻所未闻的牌子在游街。我的牌子临时换成了“坚持反动立场的地富反坏右子弟”。游街的人有的带着高帽子,有的还边走边敲锣,队伍排了半里路长,围观的群众把允山闹子挤得水泄不通。
下一个节目又是批斗,作为重点对象的我又登上了公社的批斗台,在批斗台上,一个公社的治保主任,用棕绳把我捆起来,用一根扁担把绳子反复地绞紧,然后淋上水,绞紧的绳子遇水缩得更紧,我感到一阵阵撕心裂肺的痛。我回头望了下这位如此狠毒的主任,他却狠狠地瞪了我一眼:“看什么,不认得我吧,想报复吗?”
我怎么不认识他,几个月前,他患胃溃散出血,有生命危险,急需输A型血,当时在场的公社干部不愿献血。我正好路过,是我伸出瘦弱的手臂献出了400毫升血救了他的命,我和他可算是血肉相联了,想不到他竟如此心狠手辣,还用螺旋的力学原理加害于无辜的我,用冷酷的行动来证实他阶级立场的坚定。
天气炎热,受刑后的两个手臂感染化脓了,而且麻辣火烧地痛,当地的好心人叫来公社的伤科女医生蒋医生,他给我送来了一大包草药,我每天用它洗敷伤口,药还挺管用。我至今感谢这位蒋医生,没有她的药,可能就保不住我的手,今天也不可能在此敲着键盘来回忆这段令人伤心的往事了。
次日,大队决定把我移交县治安指挥部,公安局去法办,几个民兵又将我绑送县城,一行人压着我离开了村庄,走上了“大干头”。回头看了一下我下放劳动几年的村庄,我不禁泪眼模糊。别了,山水环抱的秀丽的村庄,别了,那挺立在村口,苍翠茂密,见证历史的风水树,别了,我朝夕相处的农民兄弟,别了,我情同手足的知青战友,别了,我那上山下乡知青革命幻梦,我如今与你们永远分手了。
4天后,我被关进了公社的阶级敌人学习班;4个月后,我成了学习班通缉的一名逃犯;4年后谭XX因强奸村里的的一名少女,造成少女自杀被关进了监狱,刑满出狱后,被村里人赶出了村子,不许进村,后来病死在山上;40年后,我的手臂和心里仍然留下了历史的印记,和永远抹不去的痛。
......
又到九月九了,离
八月份写了那篇“难忘那年九月九”,还有很多想说没有说的话,文章发表在网上后看到,在那场“清理阶级队伍”的斗争中,竟有如此众多的知青难兄难弟,有如此相似的经历,他们有的已长眠在地下,永远离开了我们。比起他们,我们仍然是幸运儿,我们毕竟从苦难中走过来了。
到底我出身在一个怎样反动的家庭呢,还是让历史做个说明吧!
1979年,大学的年级主任通知我,毕业于北京大学,满怀报国志向,在1958年被打成漏网右派的父亲终于平反了。
1991年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七十周年,中央电视台播放的电视连续剧“于方舟”中,当时的河北省地下党书记于“于方周”说出了我祖父作为一名正直的知识分子—当时华北新闻的总编辑,在白色恐怖中,冒着生命危险,多次营救地下党员的事实,其中有不少是中央领导同志。
2001年天津市政协出版了近代天津名人丛书,祖父作为“不平常的报人”入选,原书指出:“他终身从事新闻事业,而且与马千里、于方周等人一道参加五四运动;亲聆了孙中山先生的教诲;得到冯玉祥的信任和资助;由两名共产党人介绍加入国共合作时期的国民党,数次参与营救被捕的革命同志;并与《新天津报》的刘髯公、《大公报》的张季鸾两度开展论战;在军阀混战下苦苦挣扎……天津报人中有这样传奇经历的人实不多见,故本书选他作为近代天津十二报人之一。”
这就是我家几代人背着的历史的“原罪”,它压在我家身上几十年,这公平吗? 不,不说这些了。
又到九月九了,农历的九月九是重阳节。星移斗转又重阳,怀旧断情肠。让我们不忘这段知青情节,怀念那些在苦难中远离我们而去的知青弟兄;也让我们关心目前仍处在困境中的惺惺相惜的知青战友,伸出手来,为他们做些什么……
难忘那年九月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