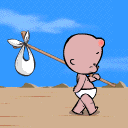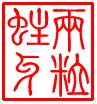一位海外知青的安宁情愫
蔡为民
“遥远的东方有一条龙,它的名字叫中国……”手机响了,这是我设置的呼入音乐信号。己快到夜里十一点了,谁会打电话给我?勿忙按下接收键,耳边传来一个熟悉的声音:“蔡为民,你好!我是杨裴伦,我想和你商量件事情。知青出书,程约汉打电话给我,要进行采访,不知他怎么知道我寄钱接济桃花村何大嬷的事。我极不愿意张扬以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从来就怕抛头露面。这件事是我发自内心自愿去做的,因为我同情何大嬷的遭遇。下乡那几年,她们全家对我都很好。是接受采访,还是拒绝采访?你帮我出个主意……”
我眼前浮现出他的面容:红润的脸上,带着腼腆而羞涩的微笑,大大的双眸闪动着真挚和睿智的光亮,永远质朴而又整洁的着装……。
我略加思索,立马拿出了我的主意:“裴伦,我认为应该接受采访,这不仅仅是你个人做的好事,这件事情既然己经传开,就不可能保密。它是我们知青和安宁农民之间深厚情意的写照,很典型,很有代表性,是历史的见证……”“好嘛,让我再想想。”又聊些其他事情,挂断了电话。
这个来自香港的电话,搅得我深夜难眠,许多远远近近的往事,象拉开闸门的水一泻而来……
我与裴伦相识于1965年9月下乡一周年总结表彰大会的第一天。全体1964年下乡知青被召集到县城开总结大会。知青们各自背着行李云集安宁县城,每人领上一床草席,不分大队,只分男女,在指定的房间里,一个挨着一个象排芋头似的席地而宿。我和他素不相识,竟挤在县文化馆的一间房子里头挨着头睡了三个晚上。白天紧张的开会,认真地听县委领导、团市委领导的报告,听八个标兵和先进集体户代表的事迹发言,晚上小组讨论和开联欢会。开会期间我们并没有交谈过,仅在分手时互相通报了姓名、村名,客气地互道:“再见,来玩。”就此分手。没想到这次偶然的相识,让我们的友谊一直延续到40多年后的今天。
裴伦出身于知识分子家庭,父母都在大学教书。再往上溯源,祖父、外祖父都是历史上的名人。1964年他自愿报名到安宁当知青,1971年招工到昆明市煤建公司五华煤管处当调货员,1987年到香港工作尔后定居于加拿大。我与他交往的几十年中,从未听他发过牢骚,抱怨过父母,诅咒过命运。在农村与农民一起背猪厩粪不嫌臭不怕脏。进城后当调货员每天骑着单车跑货场煤店,又灰又累,从来都是乐呵呵的毫无怨言。
由于从小爱好弹钢琴,裴伦返城后每天都孜孜不倦地坚持练琴,千方百计地拜能者为师,经过多年的努力,琴技有了很大提高。到了香港后,教人弹琴竟成了他的谋生之道。
1989年8月我因有事到香港,亲眼看到他艰苦的工作,每天早上九点要忙到晚上九点。听他说一年只在春节期间休息三天。记得那天我打电话给他,相约见面,他因有课,叫爱人到红堪车站去接我。来到他家后,一晚上只能抽空讲几句话,连吃饭的时间都没有。他的住房并不大,仅50多平方米,陈设也很简单。但他都相当满足地说:“初到香港时是租棚子住,现在好多了。”我确实看到内地移民一家人挤在窄小的棚户内拥挤不堪的生活,每天要打两三份工。其艰苦和辛苦程度令人为之感叹:“何必非要到资本主义社会求生存呢?”由于裴伦乐观的面对现实,找准了自己的位置,确信自己的优势就在教授钢琴的初级水平这个阶段。为拓展视野和见识,他经常去听钢琴演奏会,请教名师,探索弹钢琴的奥妙,刻苦专研,独辟蹊径,总结出一套简洁易学的授琴方法。凡师从他的弟子,进步很快,深受家长们的赞赏。由于家长们互相介绍,本不是科班出身的他声名鹊起,多年以来,生源从未间断过。值得一提的是,其中有一位香港著名演员的子女竟在他的教练下夺得当地钢琴演奏比赛的第一名,令业内人士刮目相看。
裴伦助人为乐,早已有之,并非心血来潮或追求名利。我自己就曾得过他的帮助。1966年“文革”开始时,我读大学的哥哥突然冒雨来到清水河,诉说被安排在最后一批到北京接受伟大领袖毛主席检阅红卫兵的名单中。“黑五类”子女能有此殊荣,真是十分难得的机遇,那种激动的心情可想而知。无奈囊中羞涩,身无分文,父母又不在昆明,我这个当知青的弟弟又穷得叮当响。当时我们生产队的工分值仅壹角多钱,辛苦一年,扣除口粮钱和集体户的生活费,个人基本无钱了。周围的人情况都不好,急得我团团转。想来想去只有跑到桃花村去向裴伦借30元。现在的30元不够请人吃顿饭,可那时的30元是一般工薪族一个月的工资。几年以后,我情况好转,要赔钱给他,他坚决不要。我请他给我一次表达心意的机会,他才勉强接受我养的一支壮母鸡和一提箩番茄。
何大嬷已经记不清裴伦接济了她多少钱,大部分用在打水泥晒场,建盖厨房。初略估计,17年间当是两万元以上了。这对富豪来说是区区一点小钱,对工薪阶层和贫困的村民而言是一个很大的数额。最为可贵的是相隔千山万水,在香港工作的裴伦能够在每年春节来临之际,从心里惦记着何大嬷,每当我表示深深的敬佩之情时,他很随意地说:“如果我仍在昆明单位里上班,也许和很多人一样,拿着退养工资生活,今年满60岁才能正式办理退休,也不可能帮助何大嬷那么多钱。我现在有能力去做这件事,去报答对我好过的人。”没有豪言壮语,没有激情,语气平淡而真诚。
我们1964年下乡知青与安宁农民之间纯真友谊的故事很多。七年多相濡与沫的生活,共同经历了许多风风雨雨,农民把知青当做亲人。无论在乡下,还是进城后,环境改变了,那份真情始终保持着。有的知青甚至扎根在这片红土地上,与当地农民相结合,一辈子成了安宁人。
(作者为1964年昆明市下乡安宁知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