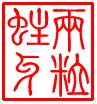忽然想起了性,我知道这很糟糕,这是很犯忌的。
为什么不能把性事当作花事呢?
阳光下的花朵向人们裸露的不是别的,正是被国人至少在嘴上深恶痛切的性。人类的性事与花事一样,都是在他们生命最美丽也最灿烂的时期,尽管人类的性事不能如花朵般展示在阳光下,但在两人世界里,却是无妨将它作为花事的。这类事儿老外做得很好,他们在公开场合说热爱性事就象我们在公开场合说热爱祖国一样坦然。如有的老外说性是一切内驱力的根源,有的老外说性是人类活动的中心,是战争的原因,是爱情是和平的目的。我们对性却是如此表达:白天把性当成垃圾,夜晚把性当成晚餐。
我知道,要把人类的性事当作花事是会大招鞭鞑的。但是,那就把它当作暗夜的花事吧!在生殖行为上这两者完全是同一回事。至于美和丑,也许更与人们的内心有关,一颗肮脏的灵魂看到的是丑陋,而一颗纯净的灵魂看到的是生命是神圣是美丽!
1、
所有性的萌发过程都呈现着一种迷蒙而又诱人的状态。
我不能准确地想起我的性启蒙是什么时候,我能够想得起的与性有关的事情是在我十来岁的时候
那是在一个夏天的早晨,天刚发亮,我们很多小孩在卖豆腐的店门口排成一条长龙。孩子们都在说最近哪儿有电影看最近又看了什么电影,聊以打发时光。忽然有高个的男孩子作引颈踮足状,接着就有其他孩子学着样,我跟着他们望过去,我不知道他们在看什么,因为我个太矮。但我知道他们关注的是在马路对面的政治干校里的一扇窗户,那窗户是敞着的,亮着灯,那窗户里有什么呢?
一会儿就有了鼓噪声,就有人赞叹说好大好大好漂亮好漂亮。我从伙伴们的赞叹声里知道他们可能是在说女人,但什么好大我却是懵懵然。我问旁边的孩子什么好大,那男孩不屑的看我一眼,告诉你也没有用。我反问道那你看见了就有用了?那男孩说你还没有那大妹子的奶高呢!你说你看了有什么用?
但是我还是和伙伴们一样,踮脚扯脖子的仰望着,当然我什么也没有看到,这让我有点失落。于是我说我会长高的,等我长高了就自己看得到了。
等你长高了你还有份,人家早做妈妈了!
我拼命解释说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我也会长很高很高。我长很高了看什么东西就不要踮脚扯颈根了。
那你会长她楼上的窗户那样高?
我不说话了,因为我知道我不能长到楼上的窗户那么高。后来我分析孩子们看到的当是一个戴着乳罩早起梳头的姑娘。只是那时我就是看到了我也肯定没有感觉。
这是我第一次看到身旁的人在偷看半裸的姑娘,尽管我当时一片浑沌,但是按照弗洛伊德与歌德的关于性的潜意识的对话,我想我在潜意识里是一定在渴望着与异性亲近的,只是我没有察觉罢了。所以我还是认定这或许就是我的性的启蒙,
2、
我有一种犯罪感,虽然我的起意是要去看那如水的月光。
你要感受月光如水的境界,你就必须去我下乡的那个山村。
我下乡的山村三面是高山,唯东面是一凹口,凹口外是一陡壁,有小溪顺着凹口缓缓地流然后就呼啸而下,在陡壁上舞出一条窄窄的白练也似的飞瀑,然后在陡壁下溅出一深塘。更远处则是一广阔的“洞”(村民对山中平地的简称)。有月亮的晚上,不管是缺月或是圆月,都是从凹口间爬了上来,在凹口旁那两株高大的杉树梢上歇息片刻。逢上有风的夜晚,就感觉不出是杉树在晃动还是月亮在晃动。
我住在楼上,窗斜对着凹口,有月亮的晚上我就会将插在墙缝里的竹篾片火戳灭,体会楼板上的这一方月光,看这月光缓缓移动。这月光先是投射在木板墙上的,然后渐渐地下移至楼板上然后至窗下,然后悄然滑出窗外。
以前看月亮时还边看边唱歌,后来社员说我唱歌象狼,吓得队上的母鸡都不下蛋了,我就只看月亮不唱歌了。
别处的月光是从天上洒下来的,我们这儿因为地势高,月亮升起的山头低于我们村的凹口,所以我们这儿的月光是从凹口水一样漫上来的,它先是将我们山下那广阔的原野灌满,然后再一点一点的往凹口处涨上来,涨到凹口时就哗啦一下涌上来,刹那间就把原本黑黝黝的小山村浸泡在这水一般的月光中。
但是那夜里我却确实听到了水响!
我将头探出窗外……
一个少女,一个赤裸裸的少女在洗澡,在这白晃晃的一片月色中,一个赤裸裸的少女在洗澡(我们下乡的地方不论男女都有在户外洗澡的习俗)!
我听见了我的心跳,这是我下乡的第二年,十八岁!
我只是在第一眼的窥探中因为惊讶而把头缩了回来。然后我就连眼睛都忘记眨了。
十八岁,一个和女孩碰一下手都要脸红半天的少年,却在无人处将他的真实表达得如此充分。
从这一天起,我开始想女人。
3、
有些的真实听起来却更象是谎言。
那年我在军马场实习,帮助军马场转为畜牧场作些移交工作。
这里大部分职工都是长沙知青,是我的老乡,他们都是从全省各地被招到这儿来的。军马场撤了后他们全都回原藉长沙,享受军人的复原待遇。这于他们是桩意外的幸运,要不他们就得终老他乡了。
我在这里如鱼得水。我的行事方法很容易被大家接受:你们把公家的东西变为私人财物时,最好把我蒙在鼓里,我肯定不主动干涉。
有一哥们与我投缘,他悄悄告诉我说,这附近有个知青妹子,七五年下的,才十九岁,挺漂亮的,他追了大半年,上不了手,现在要回家了,肯定没有戏,所以就把革命的红旗交给我,让我去试试。
我说去啊,谁怕谁啊!
朋友没有骗我,这姑娘的确漂亮,不过细看的话就会发现姑娘的鼻翼旁有细细的雀斑,这雀斑在晚上是看不出来的,蒙胧的夜色与祛斑粉将她的面容修饰得格外妩媚格外动人。我发现姑娘脸上有雀斑是第三次见面了。
那天我从场部开完会回连队,就有人告诉我说有个姑娘来找我。我知道是谁,立即踩着自行车去追,大约追了四五里路时将她追着了。我悄悄地靠上去,然后将自行车前轮往她身前一挡,她往旁边一跳,抬起头要嚷嚷时,我就看见她鼻翼旁惊出些细细密密的汗珠,那汗珠里还混着隐隐的雀斑。我当时就想这姑娘没有这雀斑一定还没有这样迷人。我就爱她脸上这隐隐的雀斑。
大约半个月后的一个傍晚,我去姑娘队上。她问我吃饭没有,我说没有,我说自行车坏了,我走路来的。所以来晚了。姑娘说还有剩饭,再帮我煎两个蛋。我说行。
姑娘是烧煤,我站在旁边看她煎蛋。她敲了两个蛋后,马上将盐(粗盐)放在蛋上。我是老知青了,自然知道这样煎的蛋是不能吃的,忙叫她赶快把盐清开敲碎再洒点水,她却已经一锅铲敲下去。我也懵了,竟然忘了就叫她干脆放点水,做荷包蛋汤,就任她盛下两个煎蛋。这自然是不能吃的,我就嚼干饭,她在一旁抿着嘴儿笑。那时特能吃,硬是嚼了一大碗干饭还不够,姑娘又去社员家盛了饭来,这回她讨了点坛子菜来给我送饭。
吃罢饭后我们就闲聊,聊天聊地聊人生当然也聊海誓山盟,越聊两人就坐得越近乎,于是渐渐地我就不太老实了,渐渐地两人就拥到一起了。
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了,反正鸡叫了。我说这么晚了,还有十来里路呢。她说那就睡这儿吧。
这时候煤油灯忽然也渐渐地暗了下去,我说加点煤油吧。姑娘说没有煤油了。
我说你睡吧。说话间煤油灯灭了,好在窗口尚可透入点夜光,人影依稀可辨。
……
我不能说得更详细了,那样会有黄色小说的嫌疑。不过我要说的是这结局肯定不能被人接受,姑娘是赤裸着身子的,但我却只是除去了罩衣。我们相拥着度过了大约一个多小时的时间。在我们相拥的时候我们两个人一直都在发抖。最后我坚持不住了,我爬起来,乘着夜色回了军马场。
很多年后我回想这一幕时,我肯定自己可以当牧师,我想除了牧师是没有办法阻止住本能那强大的力量的。而我当时全部意志力的来源是:我不能破她的身子,我必须对她的一生负责,不然她这一辈子就永远不能被招工永远不能考大学了。
这三件琐碎就是我的童年到青年时期的性史了。我想我有理由认为性是美丽的,甚至于包括自己的偷窥--我知道这很荒谬--但这夜的月光因此而丰富了我的人生;而美丽的性也只需要这样一个前提:在爱的前提下顺从本能的意志。但是我没有顺从本能的意志,我虽然一直以苦涩的心态嘲弄自己,但我内心对自己是有种自豪感的:因为我还将本能交付在良知的掌控之中。
我不是西方人,我没有西方人对待性事的那种从容豁达,我也不可能如西方人一样行事,要不就没有我与姑娘相拥良久而不冲破最后堤防的苦难经历----是的,那是百分之两百的苦难经历!我也不象东方人,因为我认为人类的性事应该等同于花事,他们都具有摄人魂魄的美丽。
还是那句话,性-爱是暗夜的花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