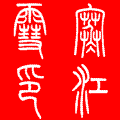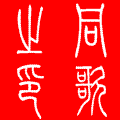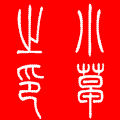我的故事(三)
由于身体条件好,农村里那些重活、笨活难不倒我;只要能劳动,生产队在工分待遇上一视同仁,特别在人格上与社员们平等,少了很多烦恼,少了你争我斗,少了心灵的革命;乡下虽没有城市的喧哗,虽没有方便的商店、电影院、文化娱乐场所和令人陶醉的风景区,但我心安定后,在各个生产、生活细节上去努力适应环境,经常与那些原来当过校长,现在为“五类分子”的人比,他们干起活来与农民没有二样,在不批斗他们时,在田里一样笑语连连,贫下中农没有谁干预他们讲话。我想我的人格比他们要高,是毛主席要我们来的,在这帮单纯的农民中间,我能够找到自己的快乐。
一年、二年、三年,那种刚下乡的的好奇感觉渐渐地消失得无影无踪。每天重复着机械式的劳动,随着对当地的熟悉,下乡当时的那种如诗如画的田园农家景象也变得黯然失色。一种被城市抛弃的孤独感,经常烦恼着我的心,想起“出身不好”回城很难,也设想假如回城后又会受歧视的情景,自己陷入惶惶不安的困境。知青们都认为前途暗淡,出路渺茫。混时度日的想法不时地占驻我的脑海。就在困惑、徘徊时,我现在的这个老婆的出现了,给了我一些安慰。她们家就住在我们知青组隔壁,家境贫寒,倒也过得自在,八姊妹只有一个小男孩,女孩从来不受宠爱,自生自灭,只会拼命帮家里挣工分,从来不知奢侈是回什么事。女孩们“大年初一就被逼着去芦苇山检柴火,冬天从来没穿过袜子,一条单裤御寒冬,一件内衣(褂子)补得象老和尚的百衲衣。十五六岁以上的三个女孩就只一件没补的衣服,在需要出众时,大家轮流穿。由于天生遗传,她们有着马来南方人种典型特征,有着几十代益阳山区山清水秀之间蕴成的纯洁,几个姊妹个个皮肤白晰,脸色红润,个个象出水芙蓉一般,在生产队,属漂亮的一族。她们勤劳,能干,朴素,善良。社员们开玩笑说,捉猪看娘种(她妈很能干),他们家女儿随便找一个都是出色的。
我是什么时候开始注意她们的呢?那时,我们知青组的几个人表现都很好,劳动很认真,但自己摆弄的生活确实一塌糊涂,天雨没柴烧就扯屋茅草,再不就发饼充饥,青黄不接时,干辣椒打汤也不是奇怪的事。劳累回来,还得自己缝补浆洗。很是烦恼。我现在的岳母,心地善良,经常跟我们送些小菜,我岳父在吃的方面与我们知青臭味相投,田里的螺鮀鳝鱼,猫、蛇、牛肝狗肺,什么都吃,遇到队里死牛,那些无人要的牛内脏、牛鞭之类的东西如获似宝,拿回来搞得干干净净,第一个叫的就是我们知青,吃罢之余,还大有兴趣地跟我们讨论“社会主义”的话题,“勒”得我们前仰后合,这时我发现有那么几双眼睛在偷窥着我们的快乐。长期的邻居生活,我们“两家”有了很深的了解,虽文化层次不同,但在面对生产劳动方面我们达成了很多默契。我发现,有她们家姊妹在旁边插秧、割谷,我们赶不上她们时,有人帮我“带上一二蔸”使你与她齐头并进,在田间“狗爬式”除草时,也经常发现一把乱草放在前面,让你踩个够而引来一片欢笑声。
渐渐地我就发现她们家大女二女很注意我们言行,出工总是想分在一组,劳动总想干在一起。我那时担任团支书记,经常晚上在大队开会、搞活动,她家大妹子是妇女队长,每次开会同去同回,开始就有些想牵手过沟,“不看见走路,等一等”之类的亲热,因为他大女已找好对象,我在这方面表现的很麻木,直到某一天,她大女突然提起要退掉那婚姻时,我才感到问题在变化,她向我借236元钱,要退掉那个男孩。我的天!那对我来说简直是天文数字,我要四、五年劳动的工分钱才能奏上它,何况去拆散别人姻缘也是不道德的呀,我无法满足她,她带着遗憾出嫁了。二女,就是现在的老婆,比他姐性格更好,更吸引人,他姐出嫁后,队里选她为妇女队长,我们照样开会,搞活动。知青组也经常晚上教她们唱歌什么的,经过一段接触后,我才发现对我真正有了感情的是她。有一天我问她“放人家”(找对象)没有?她说她妈准备把她看给临队某男孩,她不想。我问她想找个什么样的人?她笑着说:想找姓角的(牛就有角,暗指刘),我装着不懂,问他是哪里人?她说着远在天边,近在眼前,之后她就调皮地跑远了。我看到了她脸上的红晕,也尝试了她那种渴望自由、幸福的大胆。我陷入深深的忧郁之中。之前,在回长沙时在我妈和姐面前赌气说过,反正出身不好,找个乡里妹子结婚算了,曾遭到一餐臭骂。使我放弃了这种“邪念”。而面对现实,我难以决断。
我们还是装着没事地交往着,她经常主动上门来搜我的脏衣服,帮我钉扣,补丁,家里有好吃的,如酸豆角、黄瓜之类,有意夹一满碗来串门,我知道她已是有那么个意思了。我不想急于表态,我在思考着我的将来,我在寻找着我们之间的共同点。加上我的沙阳朋友也不反对,我想把这事拖一拖。而她父亲好象知道什么似的,跟她讲,晚上刘家里不去大队开会,不许单独一个人去,晚上不是到知青家玩的话,不许到其他人家里串门。我修铁路时有意买过几斤烤烟送他,我相信他对我已没有拒绝之意。直到有一天,她突然跑到我那里,神密兮兮地告诉我,她妈要把她放给临队的男孩。那家准备请人说亲。她问我有何打算?我说那你就听你妈的话吧时,她满眼泪水不知所措词。为不伤她那颗纯洁的心,也为了我们之间的感情,我作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决心娶她作老婆。我安慰她,叫她放心。她妈跟那个临队的男孩的娘是“结拜姊妹”,在小时侯就开玩笑讲过将来结亲家。她妈虽对我们之间的事有所闻,但总以为是玩笑一场,而她那结拜姊妹之间的承诺是很看重的。于是乎,就催生了“讨堂客”这样一个笑人的故事:在我老婆上门给信息不久的一天下午,她家的锅盖烂了,她妈来我们知青屋找钉子,我壮着胆子问她,你家二女放给我好吗?我们之间已有了感情。一世从没有过的尴尬使我手足无措,希望她快点回答而转话题。她不紧不慢,挤出了一句,女儿的婚姻事,我不管,由她父亲作主,她大女就是因为作主看的人家不好,埋怨大人。似乎拒绝,又好象有点希望,我恳求她,把我的想法告诉她父亲。她勉强同意。我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等待“结果”------我对她女有感情了,我将大不违地面对将来。
第二天中午收工,她父亲叫我与他同行,我受到他毫不隐讳的考问,无非是:你们家全是知识分子,看不看得起;今后是打算长期在乡里,还是上去;上去以后,带她去吗;你文化水平高,她没读什么书,你将来嫌弃她吗?我作了我不想上去,上去了一定让她幸福,不会亏待她的承诺。他爽快地把他二女儿许给了我。我诸然轻易讨到了“堂客”。
接下来的土洋接合,一顿乱搞也叫人捧腹。这事不敢向我家里人张扬,怕被阻拦。我麻起胆子执行着乡村讨堂客的程序,唯一能商量的人就是沙阳了。首先买二包沅水烟请她满舅娭姆(日本人,热情人士)作媒,履行无媒不成亲的老训,在长沙买两双塑料凉鞋(那时是稀世之宝)一双给她妈,一双给她,带着她在安乡街上与沙阳和另一个男生一道,在安乡饭店吃了一餐饭算作告白天下,在沙阳的参谋下,花二十元买一条“毛笔机”上等裤料(沙阳对“毛笔机”情有独锺,他爸一条毛笔机穿一世,给他带到乡里后,改成短裤后又穿了若干年。实践证明她这条裤穿了二十多年。)作为定亲礼物。这样她就正式成为了我的未婚妻。糊里糊涂地定亲后,我开始感到多了一份责任,以后经常给她一些小钱,使她摆脱了“轮穿衣服,没有袜子,单裤御寒”的困境,略加打扮,在年轻妹子中出人头地的显得漂亮了很多。至于怎样结婚,建一个属于自己的家,我心中一片渺茫。“泥巴萝卜,吃一截,开一截”边走边看了。后来我被调水利修防会后,结婚的问题也就解决了。
那是1972年秋天,公社书记视察大队工作,晚上要在沙阳过夜,我当时是团支部书记兼小学代课老师。我那天接待了他,把老师的干净铺让给他睡,聊天时,他说大队搞没意思,问我去不去修防会,当时的修防会是很好的事业单位,我同意后,他说,你明天去找华富(修防会主任),就说我安排你在修防会上班。工资定36元。别人18、20元要二年学徒工后才29。5元,再三年才36元,可见那时他给我的优惠。第二天就来到水利单位。一来就显现了一定的工作能力,办简报,搜集进度、好人好事,重大新闻,通知开会,作会议记录,一个人干了三个人的事,没出过差错。受到公社干部和修防会领导的好评。冬修后,我由文员改为工程员,开始了我长达30几年的工程技术业务生涯。
再回到我结婚的问题上来。那是1973年的冬修,快近年关的腊月二十四,天上下着鹅毛大雪,冬修全部停工,修防会一行人从虾叭出发,全面看一下工程情况,回杜家铺修防点,准备开年终会放假。傍晚,坐在火炉边聊天,李华富主任突然冒出一句,问我想不想结婚,(我找农村姑娘一家喻户晓),我不知怎么回答,他说你不管,想结婚我们帮你办。讲话后,马上派一名副主任,用箩筐背着单位分的鱼肉,陡步来到我岳父家,进门就说,你们作好思想准备,明天去结婚登记,后天结婚。我岳父不知哪里来的风,说你们冒搞错吧?是讲笑话吧?我什么嫁装都没有,被子都没有弹,怎么结婚呢?我们单位那当家的说,一切都免,结革命婚。修防会全部帮忙搞定。我岳父将信将疑,喃喃自语道,我看你们禾十结着?我从身上排出十张十元大钞,要我老婆明天买点衣服, 说登记后,随便结一下算了。我老婆一脸的惊异。第二天一早,我邀她去公社,她说没有这样结婚的,她不去,我当着他妈说,你到底结不结?不然我就回长沙过年去了,她妈骂了她几句后,便乖乖地跟着我来到公社,随着一包喜糖往管民政干部桌上一丢,几分钟就拿到结婚证,刚好供销社易主任在公社,我请他帮忙开了烟和糖(要计划)的便条,来到县城,买了几件衣裤,带着喜悦,两人一路情话走回家来,回家时已到了夜晚。回修防会一路小跑,庆喜今天办事顺利。
第二天(古历二十六)一早,搬来一床修防会防汛抢险用的被子,同志们每人出点钱帮我买的被套、垫单什么的,把新房布置得象模象样。随着大队书记和民兵营长带领各小队妇女队长、民兵排长的一阵锣鼓,把新娘送过来了。六桌饭菜,73。5元的开支,我扣了四、五个月,那年过年,我两留守单位,自己煮自己吃,享受了从来没有过的乐趣和幸福。春节后,公社知青办又拨给我一个立方米的杉木,我用我家里给我寄来的几百元钱,社员帮忙在本队做了一栋茅屋,搬了几件知青家具,便有了一个自己的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