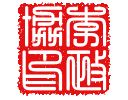创业艰难百战多
——记优秀民营企业家王时清的创业心路
因为工作的缘故,认识王时清已有十多年时间了,并且因性情投缘,初交后便成了难以忘怀的朋友之一。其间风雨沧桑,星移斗转,各自为自己的事业奔波、忙碌,确实离多聚少,彼此都经历了太多的磨难,饱尝了失败的辛酸和成功的喜悦,共同见证了世纪伟人邓小平南巡后中国大地特别是永兴城乡所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在随后的日子里,由于他事业越做越大,见面的日子便难能可贵了,偶尔相遇一次,闲聊中他的手机也是常常铃声不断,有来自政界的,有来自家乡熟人的,更多的是生意场上的客户,除国内各省市外,美国、英国、法国、比利时、日本等国的客户之间的联系也是家常便饭。放在二十年前,这些都可说是天方夜谭的故事,但现在却切切实实地发生在这位来自于地地道道农家的中年汉子身上。无论事业如何如日中天,无论财富如何囤积满仓,但他依然保持着一颗平常之心,宽宽的额头里蕴藏着许多新颖的思想,深邃的目光里蕴藏着过人的智慧,略微凸显的颧骨,表现着他攻坚克难的刚毅性格,高耸的鼻梁预示着他不屑于狗苟蝇营的肖小言行,圆润的下颚更能淋漓尽致地表现出他的豁达大度和慈善心灵。曾有人多次尝试着要用概括的语言来表达永兴金银冶炼人的总体精神,但一直难以如愿,不过,我认为用“不畏艰难,敢为人先,精于博奕,工于巧变”几句话还可以稍微挨上点边。永兴冶炼人是英雄群体,但王时清无疑是其中的特殊代表之一。其实,他原本就称不上潇洒帅气,但却具有一个负责任的男子汉所具有的十分鲜明的外形特征,他的外表一如他内心的晴朗明了,如果你有绘画技巧,只消轻轻几笔就可勾勒出一幅完整的肖像画,当然,仅仅从他略嫌消瘦的身躯,你很难把他与一个拥有资产上亿元,出口创汇在郴州市排前列,铟产品产量占全球十二分之一强的优秀民营企业家划上等号。而在这拥有巨额资产,年产铟40吨多,白银200多吨,铋400余吨的民营企业家背后却有着怎样艰难曲折的奋斗史,至少笔者采访过后是内心为之动容的。
一
少年的苦难,逼迫他早挑重担,也初步显露了他不凡的管理才华。王时清1956年出生于柏林九团村一贫困农民家庭,青少年时代用苦难二字来形容一点也不过份。因为,柏林在历史上叫做白泥塘,该地域属典型的丘陵地区,略带粘性的红壤土质极易产生晴天灰满天,雨天泥沾腿的恼人环境,并且很久以来,这里就严重缺水,每到夏秋季节田地干涸,赤地百里,地里的泥土由红壤晒成了白壤,白泥塘之名也因此而生,其凄苦情状现代的柏林人根本无法想象,但从那首有多种版本的民谣中确实可以窥一斑而见全豹。其民谣道:“白泥塘白泥塘,生了儿女苦了娘,下雨泥泞喝黄汤,天旱遍地闹饥荒,拖老带少去逃荒,有女莫嫁白泥塘”。正是这恶劣的自然条件,使得早在三百多年前清时期柏林人的祖先就在走南闯北的谋生过程中凭自己的聪明才智偶然求得了从废矿渣中提炼金银等贵重金属的秘诀偏方,尽管根本无法与现在的冶炼业相比,但在当时确实是个破天荒的壮举。解放以后,由于政治和历史的原因,这一颇具神秘色彩的传统产业被高压封杀,有此技艺者胆大一些的便逃到了港、台地区,胆小一点的便封炉收手,跟着建设社会主义的滚滚洪流盲目前奔。当然,天道也有不酬勤的时候,充满理想主义的柏林人并未因社会主义改造和合作化运动而步入温饱的殿堂,而是依然挣扎于贫困潦倒之中,这里面的故事太多太多,非洋洋专著难以述其万一。王时清的父母就是其中怀着美好信仰讨生活者之一。1956年就在人民公社化运动即将揭幕的前夜,王时清漫无目的地降生了,地点是现在的柏林镇九团村一偏僻的小山窝。尽管家境贫穷,但毕竟是农家长子,住在土砖房里的这对年轻父母还是把无限的爱意和甜甜的笑意写在脸上,那段日子,王时清的父亲仿佛吃了蜜糖,喝了人参汤,吃饭吃得香,走路脚步轻,有时候还情不自禁地哼起了只有当地人才听得懂的地方小调,母亲也从此精神了许多,不但将自家的活儿料理得丁是丁,卯是卯,邻里乡亲有什么欢宴喜庆的事,她也乐得抽空帮上一把,村里人都称她是个闲不住的人。苦日子也有苦日子的过法,由于农村营养极差,导致王时清从小就不怎么长个儿,但五谷杂粮吃得多了,身体素质还算不差,三、四岁时已能跟着父母下田爬山,五、六岁时便能拾掇谷穗,打豆晒谷子了,当时村里乡亲对这个细伢子都很亲热,村里的大小事情他都跟着大人屁股后面蹦蹦巅巅的,似乎少了他还不行呢。1963年正是我国三年自然灾害最为严重的一年,王时清背着母亲用土棉布缝制的小书包跟着村里稍大些的孩子们上学了。学校就在村部,几间低矮的土屋,几条长长的松板凳,每人一块垫了稻草的土砖头,谈不上什么条件,孩子们等钟声一响,便各自拣了自己的位子直直的坐着听老师讲课。当然,那时的课程十分简单,一到三年级除了语文和算术两本薄书以外,几乎没有什么读物,到读高小时便变成了一本红宝书——毛主席语录,学习十分轻松,每天跟着老师们背着在他们那个年龄段根本无法弄懂的最高指示,迷迷登登,嘻嘻哈哈地往返于家里到学校的泥土小道,人在天天长高,知识却没见增长。象许多农村的孩子一样,学校悠闲自在,其乐融融,但回家后却是另外一番景象。放下书包,舀两碗稀饭站在锅台边咕咚咕咚喝下去,再到厢房拿把镰刀,跨上个小背篓,今天扯猪草,明天打鱼草,忙忙碌碌等到天全黑了才就着星星月亮往家赶,虽是赤脚走在窄窄的田埂上,但决然找不到现在流行歌曲所唱的那份美妙。毕竟,谋生才是人类的第一本能。
人生之路,充满急流险滩,也遍布着坎坷曲折,而这坎坷用在年幼的王时清身上,却显得过于残酷。1968年,正当他充满憧憬准备向初中学业迈进时,刚入不惑之年的父亲却因积劳成疾而撒手人寰,当时王时清才十三岁,而弟弟王时章不到四岁,家里的顶梁柱轰然坍塌,留下无依无靠的孤儿寡母,对于地处穷乡僻壤的王时清母子三人来说,其凄惨情状万难备述。但是,人生的路尽管艰难,总还得义无返顾地走下去,凭着父亲在世时良好的人缘,在众乡亲的帮助下,简朴而又庄重地处理了父亲的后世,年少的王时清一夜之间仿佛长成了大人。父亲安葬七天之后,他懂事地跑到父亲坟前,新添了几把泥土,就近折一些松树枝插在坟上,哭罢一场,回到家里郑重其事地向母亲宣布了他停学务农的决定,怕母亲伤心,他硬是强忍了心中的酸楚,根本没流一滴眼泪。母亲虽然心疼孩子,但看到年幼的时章还依偎在他身旁时,便忍痛答应了懂事的长子的请求。
十三岁,干农活肯定是不行的,怎么办?一时还找不到适合自己活儿的王时清一天傍晚蹲在屋角苦思冥想时,突然被远处一骑牛少年的悠然自得点拨开来。放牛,这可并不是个力气活,肯定拿得下。当晚王时清便向母亲谈了自己的想法,母亲第二天便向队长说了这件事,于是王时清便有了自己第一份事业——放牛。俗话说,穷人的孩子早当家,一拿上牛鞭,竟三年未丢。在放牛的过程中,他还不忘背上背篓,每天弄些猪草回来,那时的粮食紧张,养一头猪要一年时间才能出栏,因而扯猪草几乎是每个农家孩子的必修课。也正是这三年的放牛生涯初步培养了他独特的组织才能,村里其它几个生产队的放牛娃都被他组织起来了,谁把守坳口,谁把守岔路,谁的牛走在前头,谁的牛殿后,谁有病了由谁来代班,安排得井井有条,这伙天真烂漫的农村少年也很乐意听他调遣,俨然成就了他这个孩子王。
苦难的日子时间过得很是缓慢,好不容易捱过了三年牛倌生涯,到十六岁时,王时清已略显了小男人气概来,大队干部也日益看好这个聪慧、吃得苦、霸得蛮的小伙子,先是安排他当民兵排长,一年后又把生产队长的担子压在了他的肩上。别小瞧了这个生产队长,可管着百十几号人,队里社员吃穿住行、读书就医、生老病死,都得考虑,都得插手,其管理难度决不亚于管理一个小型企业。几年的磨炼,使他的管理能力和水平大有长进,并先后于1978年光荣加入了党组织,1979年又担任了大队支部委员,以至后来担任柏林农工商总公司的总经理、企业办主任等职务。一路走来一路难,一路走来一路歌,生活的艰辛,倔强的个性,已不断丰满了他闯荡事业的羽翼,一颗谁也没有预料到的企业之星就这样冉冉升起了。
二
大凡成大业者十之七八有过或大或小的挫折,王时清也是如此,在所有冶炼业主中他可算是风吹浪打一路蹒跚地走过来的,但正是创业中的挫折,铸就了他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也逐渐使他明白了好多事理。王时清的早期经历,注定他不甘寂寞,而曾经穷困的窘境,更触发了他渴望致富的神经。王时清是个爱琢磨的人,虽然他并不是天生搞企业的料,但企业天生就垂青他这一类的人。早在出集体工的时候,面对每天不足两毛钱的工日,他便在琢磨怎么弄点外快来改善生活。当然,挑炭寻黑路,挑水寻湿路,再怎么精明的人也不会放过身边最熟悉的事。由于自小喜欢摆弄农机农具,到当生产队长后他便成了当地的农机具修理的师傅了。于是,利用这一自身优势,他做的第一次赚钱的行当便是到临近乡村修理农机具。那时,搞副业是资本主义尾巴,声张不得的,他只好晚上摸黑跑到附近的洞口、龙形市乡,帮人家修理农机具,天快亮时紧赶慢赶往回奔,每天弄三、五角钱外快,心里甭提有多滋润了。王时清是个注重效率而不注重形式的人,在出集体工的当口,其他生产队都要出早工,即早晨起来搞两个小时劳动才能吃早饭,因他喜欢晚上活动抓点副业收入,早晨一般起不来,因而他这个生产队便取消了做早工的规定,大队曾对此很有看法,但由于他领导的生产队各项工作都走在全大队前头,那些想抓辫子的人也没办法下手,只好听之任之。
初尝抓副业甜头的王时清,潜藏的经济细胞慢慢活跃了起来,竟尝试着到县外去做生意,柏林本地是个穷山恶水的地方,从本地打主意是没有多少油水的。于是,他又把目光向周围的乡村扫了一遍之后,又通过走亲串友了解到衡阳、耒阳一带农村建房木料需求量大,该地大部分乡镇缺木材,而本县龙形市、樟树、洞口等乡镇,松木资源十分丰富,且由于木材当时属国家计划控制的紧俏产品,各区域间差价比较大,赚钱的机会也较多。于是,脑筋活络的王时清做的第一笔跨县生意便是贩运松板到耒阳、衡阳等地出售,开始是小打小闹,用手扶拖拉机拖一立方左右的松板去外地卖,一两次下来,虽然利润不多,但也有了上千元的积蓄,当时的上千元确实不是个小数目,因为万元户就可以响亮一方了,而为了成为万元户,王时清几乎做了几年的好梦。看看松板生意做得还比较顺畅,有一次他便干起了大买卖,弄了一辆江西嘎斯车满满的装运了一车松板往耒阳南厢驶出,当晚从耒阳东湖沿浔江方向颠颠簸簸到了高炉乡地段时,前面出现了一辆灯光时明时灭的吉普车,当他的车小心翼翼往前挪动时,对面突然下来两个人,他们挥着印着红黄标志的图牌,并不停地打着车辆靠边的手势。“糟了,遇到林业检查站的人了。”王时清下意识地打了个冷颤,车子只好慢慢地往一边靠去。对方用湛亮的三节电池的长筒手电在他身上划来挥去,仿佛战场上俘获了将领级的战俘,得意之情难以言传。由于双方都是方言土语,双方僵持了好半天也没说清个子丑寅卯,尽管王时清拿出了永兴方的木材准运证,但由于准运证所填数量与实际装运量有点出入,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也没办法说服对方,且对方这次检查人员并不是省油的灯,递烟,不抽!说好话,不听!搞小动作,没门!做生意之前,曾听人说过耒古仔霸蛮,这次算真正领教了,磨了一个多小时,车子被虎视眈眈的检查站人员拖进了高炉乡政府,接下来是卸货,开没收单,走人。
这一车松板足有五个多立方,价值1000余元,搭上盘缠,饿得肚子咕噜咕噜不说,前些时候做生意所得尽数付诸东流。
这次可以说是王时清第一次受到了生意场上的挫折,他几乎破了产,回到家一连几天没起过床。
地球依然在转,路还得走下去。稍稍回过神来的王时清又打起了别的生意经,当他了解到衡阳电厂的老总与某位生意场上的朋友有点蔡九般的亲戚时,脑瓜子一阵活络。农村当时仍是以粮为纲,而提高粮食产量的关键又是靠化肥,特别是作用最大的尿素是农村最为紧俏的物资,而在凭票供应肉食的日子里,肉鱼产品又是单位最为紧俏的物资。虽然,他当时还没能与经营化肥生产企业拉上关系,但他知道电力部门是“电老虎”,化肥企业不敢不求他,于是一场以弄到尿素为目的的迂回战术出笼了。靠着这个巧妙的战术,他将家乡的猪肉和鲜鱼送到衡阳电力公司,衡阳电力公司再利用自己的关系从化肥企业弄到了尿素,一时,王时清能弄到尿素的说法不胫而走,县里开三级扩干会时,其他公社的生产队长乃至公社书记都找上门来。于是,王时清又扩大了迂回线路,他把郴州红旗造纸厂的领导说动了,使他们同意了他的肉鱼产品换尿素的“食品换化肥计划”。往来于几家企业之间,王时清初步了解了生意场上的一些“小道道”。
正是靠着这“食品换化肥计划”的实施,才使得受了第一次挫折后的王时清有了再一次经受考验的“资本”。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步实施,农村经济能人纷纷施展自己的拳脚,干起了各种赚钱的名堂,被人称之为无中生有的传统冶炼业又死灰复燃,王时清就是柏林第一批冶炼人之一。而搞冶炼确实是个风险性难以预测的行业,经历过挫折的王时清奔东走西,好不容易凑足了本钱到江西赣州搞原材料时,却又使他遇到了生意场上的第二次“触雷”。原来,他经过多方打听,了解到江西赣州某铜矿有大量的废渣积压,当时兴冲冲赶到了该矿,看到堆积如山的矿渣,初步估计有500多吨,当时1万元/吨,需筹资500万元。他看好货后弄了些材料回来一化验,结果成色很好,赚几百万元没问题。于是,想方设法弄了500万元将这些矿渣悉数买下,但由于他是首次搞这么大的买卖。化验的成份与矿渣实际含量严重不符,选矿失败,500万元巨款就这样付之东流,望着那土丘似的矿渣,王时清呆呆地发楞,精神几乎全面崩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