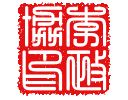何永洲
满打满算,在县文联工作已经6年了,可湾里人至今还不知道我上班的具体单位呢。因为在此之前,我在乡下一连干了整整10年的乡镇领导,才调进县文联工作的。县文联就在县委机关综合大楼办公,好些人只认县委机关大牌子,不瞧“文学艺术界联合会”这块小门牌。一传十,十传百,湾里人就说我们在县委办公,就把我当成县委机关的领导干部了,就说我从乡官提拨当县官了。
其实,并不是湾里人所想象的那样。这些年来,我深深感到,在县级文联工作是非常艰难的,除了写写文章,为业余作者看看稿件,办办有一期没一期的内刊杂志,再没其他优势了。在一些知内情的干部群众心目中,早把县文联看成了弱势群体,看成是养老的单位,休息的单位。其实也是这样,从行政职能的角度看,在全县众多部门,公章使用频率最低的,恐怕是县文联的公章。因为谁也不需要靠这个公章去解决实际问题,去获得实际利益。因此,无需我再往下讲,读者就明白不过了。文联是一个最没有权,也最没有钱的地方。在这样的地方工作你看艰难不艰难。尽管如此,单位还得生存、还得运转。那就只有靠着向那些有权的人借权,向那些有钱的人借钱,来办好文联的事情。所谓向有权的人借权,就是争取领导重视,争取领导重视是一门学问。对于一个县来说,县委书记、县长,是全县人民的书记,全县人民的县长,社会稳定是压倒一切的,发展经济是中心的中心,文艺工作不能救死扶伤,无甚关系国计民生,可能一时难以列入领导的工作日程,这是正常而有情可原的。但是,你如果能够让领导认识到:文艺工作是精神文明建设中的重要一环;你如果能够让领导认识到:文艺工作能够为社会稳定营造一种良好的环境和氛围;你如果能够让领导认识到:文艺能够使经济发展,今天的文化就是明天的经济。那么,领导就自然而然地变成了你的领导,书记就是你的书记,县长就是你的县长了!
下面我遇到的一个难题,就是通过紧紧抓住领导,采用向有权的人借权,向有钱的人借钱的方法而变通解决的呢!
那天,我正在办公室看一篇业余作者寄来的短篇小说,突然,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响过,传来对方毫无客气的告急:“洲哥,前几天连降大雨,湾里遭受了百年不遇的洪灾,你们县委领导快来看看吧……。”我脸红心跳脑壳突然膨胀起来,我算什么县委领导呢?但我知道电话是我湾里的头儿李除夕打来的。
李除夕本同我老庚,我那年5月生,他生于同年农历12月30日傍晚,正好赶上除夕之夜,全家 在过年的欢快之中又添新喜,他教过几年旧学的父亲无限感慨地说:“这可真是难忘的除夕之夜啊,就叫他除夕吧!”这样,就将我老庚定名为李除夕了。李除夕是同我穿着开裆裤,一声老庚一声哥哥喊大的。可他初中未毕业就死也不肯进学堂门了,他说读书不好玩,不自由,写作文脑壳痛。我和他同桌,他十有八九抄我的作业,抄完作业就用那种自家土制的香喷喷的干红薯皮回报我,奖赏我,每天一小口袋。数学作业抄了无所谓,很难被老师发现,可两篇作文一模一样,就很快被老师发现了,将我和除夕留校了。有一天下午放学后,我和除夕在学校办公室被老师罚站足足两个小时后,天快黑了。那时家里穷得要命,我们没条件读住校,就每天来回赶十多里山路读通学。我怕摸夜路,既不敢说是除夕抄我的作文,又不敢说吃了他的干红薯皮,急得直哭。除夕没哭。反而憋了一肚子傲气,愣头愣脑的昂起头,对正在批改作文的老师说:“是我抄了洲哥的作文。”老师抬头皱了皱眉头说:“那就请你重作吧!”除夕却鼓着青劲脸一红:“我重作个屁”!老师桌一拍,眼一瞪立刻站起了身:“非重作不可!我决定明天下午最后一节自习课改开班会,李除夕除了补交重作的作文外,还要向全班公开作出深刻检讨。”
回到家,除夕托我将留在老师房里的几本作业本带回,说他再也不踏学堂门了。开他们班会,奈得老子卵何!后来除夕真的决心务农了。除夕务农来得比读书还认真,还负责。他说务农比读书自由多了,轻松快活多了,好像他生来就不是读书的料子,是务农的坯子。日积月累真的还学得一手绝农活。且不说浸种育秧、摧肥打虫、犁耙功夫,单说插秧就令人一惊,湾里有个名为田中之王的百担丘,长宽方圆几十米,他在田埂边向对岸斜着眼睛一瞄,撒下秧苗,撅着屁股弓着腰,左手快速分秧,右手一上一下在泥水里运动,像个插秧机。一会功夫,横平直竖的禾兜,就像条标准的绿化带抵达对岸目的地。村民点点头、挤挤眼、咂咂嘴,个个服了他,只不过那些年重政治轻技术,没有谁着意看重李除夕。后来作为湾里唯一高中毕业做回乡知青的我,当了生产队长,在此期间我精心培养李除夕。再后来,我别有他务,就让他接了我的队长。加上李除夕正直无私敢说敢做,连选连任一当就是20余年,从大集体一直干到包干,从生产队长一直当到村民小组长了。李除夕今天在电话里叫我县委领导,怎不叫我脸红呢?比当初让他抄作业换干薯皮吃,被老师留校罚站时的脸还要红。以往我也接过乡下人的不少电话,有的来自我曾工作所在地的村组干部,有的来自蹲点驻户,还有来自种养个体户或兴趣相投的文友。他们大都是因为子女升学、就业、参军、建房批地基,办理林业砍伐证之类。当然还有打官司上访的,求我疏通关系打招呼的,特别是湾里人更令我心烦脑胀,因为大多是三叔六伯兼亲带故的,就更随便了。他们家人有个病痛什么的,进城入医院办手续,找熟人优惠医疗费,借钱借日常住院用品,连远在广东打工的,都握着电话遥控指挥,要我为他们代办身份证、户口……你说烦不烦脑?当然作为一名土生土长的农家子弟,对湾里人自然有一份永远难以割舍的亲情和乡情,能办到的事应该要办好,可是,凭我这地位能办多少事?何况好多事早已依规依法走上正轨,都得按政策法律规定去办哩。妻子不欢迎这些人到家里吃饭,她嫌乡下人太脏,爱喝酒聊天,当然吃餐饭没关系,没政策规定。妻子懒得下厨,我可以自己动手,或者干脆领着他们上街吃个盒饭,问题就解决了。而现如今,李除夕电话不是吃餐饭的问题。他要我去家乡看看的意思,我一听就明白了,莫非是通过我穿针引线,从上面弄笔钱或一批物资帮助救灾补损。应当说这是正常的、应该的,可对于我来说就太为难了。
晚上,我失眠了。一些陈年旧事如同记忆中的幕幕电影,魂牵梦绕挥之不去。
我湾门前有条河,常年清澈见底悠悠荡荡,河里可摸鱼钓鱼,鱼多可卖钱。在我的印象中,湾里人大多彩是吃鱼长大的。河边长满了多年禁伐的水杉树、松树和樟树,这些树不仅四季翠绿为湾里添景润色,而且护着河堤和河堤内百余亩良田。冬去春来年复一年,那片良田被憨厚勤快的湾里人整得四角四正,畦是畦埂是埂的。因为这片良田是我湾里60余户200多人口的重要生存来源之一,也是我们幼时捡禾线(稻穗),放牛的三爷爷将我们抱在牛背上学唱山歌的主要娱乐之地。不知不觉那片热土把我养大了,参加工作了。
每每逢年过节回乡,和湾里人端着粗黑大碗喝“红薯烧”时,他们就向着我没完没了的,说些前尘往事:你出生时是我和二婶接的生,刚生下你就浓眉大眼的像个男子汉;你那年摔在塘里,好在我正在塘边洗衣服,算你命大;砍柴的日子你还记得不?口干肚饿时你就带头偷人家的黄瓜、偷集体地里的红薯吃。可不是,那时,干了坏事我们就躲在牛栏楼上过夜,不敢进屋,弄得父母点着松光山脚田野河边到处喊个遍。急怒得老队长眉毛一竖,烟筒一甩,说要罚工分,湾里人就说算了算了,孩子还小,下回莫做就是了。他们还问我,你还记得我们一起唱戏么?用柴火灶上锅底黑烟灰和生产队盖章的红印油打花脸,说唱就唱,快活极了。我连连点头说记得记得。
记得那是高中毕业后,我踌躇满志,真想在广阔天地里干翻大事业。白日里和湾里人同流汗同劳动,晚上还写稿编黑板报,编成的黑板报挂在村头路边,要湾里人看形势知政策。我还带头把湾里的好人好事编成顺口溜、三句半、渔鼓词什么的,将湾里有点文化的青年男女组成了业余文艺宣传队。锣鼓法器是湾里老人从自家找出收藏多年的“古董”,二胡是自己用蛇皮蛋白蒙好的,就这样在村头自编自演起来。那些湾里的真人真事由湾里人演给湾里人看,台上台下欢喜得前仰后合,差点笑掉了牙。四叔公还用烟筒脑壳轻轻敲击我的头,摸摸长须将老拇指竖起来。半夜了,三姑六婶还快手快脚悄悄弄了米糍粑,搞来香葱鲜白菜,煮了一大锅,说演戏的饿了,都来打个夜平伙。湾里人还让我们宣传队的每天只出半天工,下午排戏,说他们想看戏,有戏看干活才有劲。想起这些,现在觉得真的好有味道。
后来湾里人还选我当了生产队长,我觉得自己终于当上了200多号人的“官”儿,心里美滋滋的。不料恰逢恢复高考,目睹一批批农村青年跨入大学、中专门槛,我就有些眼热。于是,黑板报停办了,戏班子也散了,我整天攻读ABC去了。结果呢,偏又名落孙山,但我仍不服气。后来当了民办老师,再后来转了公办老师。就和湾里人慢慢疏远了。如今想来,我当队长时既未带领湾里人致富,也未为湾里人办丁点看得见摸得着的事。而是一味想着跳出农门,真的有些对不住湾里人,总想寻找机会报答他们,心里才踏实。
现在湾里遭受了特大洪灾,我心里当然有种难以明状的不安,就想专程访故。可新的问题又来了,单位没有车。以前我总是携妻带儿,浩浩荡荡、风风光光回家过年休节,一到老家湾里人就如众星拱月围着我那部豪华的车子团团转,伸出粗大的手,在车壳车灯上,拍拍摸摸、摸摸拍拍,随后就陪着我问这问那,聊聊侃侃、侃侃聊聊,没个完,母亲每天都得多烧几壶开水。将自家黄泥地里种的那些甘甘甜甜的嫩绿茶叶耗去一大半。从前我在一个大镇当领导,那个镇真是肥得流油。镇政府有4台车,且都是像模像样的小车,最差的也是北京吉普。同时驻镇的七所八站都配上了车,还有镇属企业,个体老板的车,一台比一台“年轻”,一台比一台豪华。记得那时我一年回老家几次,有时觉得镇里的车档次太低,就伸手借用企业老板的车。借了车不算,有时还借“油”(在企业报发票)。逢年过节,我在家一住几天,还加班加点到车站接送过打工妹。父亲逢人就夸奖说,我儿这才是当上了像模像样的官儿,你看,连车子都一年一个样,一年比一年高级。他高兴而十分得意地用老粗的手,在车身上这儿摸摸,那儿敲敲,这“乌龟壳”,据说至少得值几十万元哩!而如今呢,进了文联这清水衙门,连车轮子都摸不到一块。记得调进文联的头一年春节,不知是我们习惯了在老家过年,还是那来的冲动和决心,单位没有车,我就冒着大雨带了妻儿坐公汽回乡了,县城离老家75公里多,下公汽后还要走上两三里村道,我们踏着坑洼泥淋村道往前走,连年货都被雨打湿了。回到老家屁股没坐稳,父亲就问:你的车子呢?司机呢?妻子做了个鬼脸瞧瞧我,好像在示意我千万别向父亲 说实情,怕老人家失望。我会意地对父亲说,车了正在城里维修保养哩,一时用不着!……
从那年起我就再也没去过老家过年过节了,顶多让儿女去应付应付,看看长辈。这回呢,看在乡亲们的份上,不去实在不行了。为使脸上有光,还是借台车吧,我终于拨通了几个熟悉单位的电话。可这些单位听说文联要借车就大打折扣了。这儿说局长要用车,那儿说书记正用着,还有的叫苦连天,不是说没钱买油,就是说年久失修车子开不动。那口气,好像比文联还要穷。既然是这样的情况,既然是这种预料不到的结局,那就没必要打扰人家了。我气愤地将话筒放得卡察一声响,甘拜下风的在心里咕噜了几句,他*的都是些视利眼,老子干脆租车算了,难得受这份窝囊气。
我在出租停车场瞧了瞧,选好一台油亮崭新的“桑塔拉”,车没什么说的,和我以前坐的相差无几,可就是那棚顶上“出租”二字伤脑筋,我就和司机商量是否能把车棚顶上写着“出租”二字的三角牌牌取下,司机不解地问我为什么?我说是为了执行一项特殊任务,取下牌牌办事要方便些,并答应另加司机20元取牌费,司机基本同意了。其实我是想取牌后湾里人就把“桑塔拉”当成我单位的车了,我脸上有光。此时,我的手机突然响了,对方的声音好像很熟悉,他说他是李除云(李除夕的老弟),从深圳回老家来办户口迁移证,要我带他到公安局户政股一趟,他带私车来的,正在路上,约莫半小时到达。事情往往就如此巧合,我兴奋而礼貌地招呼出租车司机,说我有急事要处理,下回才租他的车,急忙谢了走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