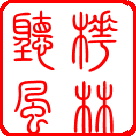四类分子
刚到大围山就有人告诉我们,那个每天赶着一头牛优哉游哉、别的啥农活也不会的人是个四类分子,这无疑让我们用别样的眼光来审视他。
四类分子莫约六十多岁,刮瘦的,勾着背、低着头、两个肩耸起来,衣服穿在颀长的身上好像是挂在衣架子上,有一种空荡荡的感觉。 此人言语不多,偶尔与人说话则沙哑着喉咙细声细气,脸上挂着笑容和颜悦色,从来也不与别人较真,好像生来就没有脾气,用如今的话来说也许就是没有个性吧。
我们知青组是住在一个大屋里,与四类分子家的门隔着一个堂屋,两扇门相互对着,经常是一开门就打个正照面,每当这时他会面带恭谦地退了回去让我们先走,这样倒叫我感觉浑身不自在,后来我一想,可能因为他是四类分子,看到我们这些响应党的号召从城里来的谓之“知识青年”的人,有点敬而远之?他怕是自觉地和我们保持着距离吧?
至于他究竟属于四类中的哪一类我一直没搞清楚,问了袁婆婆和谢大嫂她们也都含糊其词讲不清白,又问队长和团支书终略得知一二,原来因他家祖父曾是办私塾的,从小他跟着祖父识字;后来又到长沙去上过学,解放前还当过几天国民党的户籍;土改时又因他家的地比别人多,于是给划了个富农。划成富农也罢了,可他还时常抱着个书本啃呀啃的,这且不是和贫下中农格格不入吗? 最主要是他不擅农活,用农民的话来说是:“嘛里都搞不得”,怎么看他也不太像个农民,就因为这些原因,多年前,四类分子的婆娘跟着别的男人走了。
但这四类分子有一长处,毛笔字写得极好,逢年过节各家各户门上的对联,还有哪家有红白喜事要写个什么帖子,就连队上要出个什么财务公布表格、写个什么标语的,全是他的事,只有在这个时候,他的背就好像伸直了许多,只见他熟练的把那些红纸白纸折好格子,铺了开来,瘦长的手指捏着毛笔,一改平时的窝囊相,满脸自信的表情,那笔在他手里运筹自如,一点不像他拿锄头的样子,而且下笔抑扬顿挫,那字写出来真是漂亮,让那些围观的人连连点头,“啧啧”不已,这使得我也不得不对他刮目相看。
因为四类分子干不了别的什么活,队长就安排他饲养队里的一头母黄牛,这活他还真干得叫人没话可说,一年四季他的生活是以牛为中心的,每天一大早就牵着黄牛出门去吃露水草。夏天,他手里晃着一个自己用东茅草做的掸子,跟在牛屁股后面给黄牛驱赶身上的牛虻,傍晚,社员们都收工了,才见他跟在牛屁股后慢慢的踱回来。 赶上农忙季节,队上要使唤用牛了,他会心疼要命,跟着牛到田边,深怕用牛人的鞭子会抽得太重,牛一收工,就被他赶紧牵到河边洗抹干净。 冬天,他会把牛栏铺得暖暖活活的,准备好多干粮给牛过冬。 那牛呀,硬是被他养得膘肥体壮,浑身油光光的缎子一般,连队长也常拍拍那牛滚瓜溜圆的身子,呵呵地直点头。
可没想到后来,四类分子可就因为这牛到了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