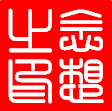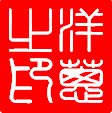那 年 下 乡
姐姐在家里排行老大,是六四年下放到江永的。
姐姐聪明,能干,还漂亮,读书不费力,于是就不算蛮发狠。印象深的有件事,她在自己的一个本子封面上,很潇洒地写了“随心所欲”四个大字,被我父亲狠狠地说过好几回。现在想来也是,那年月,谁能随心所欲?稍微懂点事后,谁还敢随心所欲!这实在是处于青春期的女孩子一厢情愿的小浪漫罢了。
高中没考上,我们谁也没有怀疑是“政审”差了分(可能我父亲除外),只是觉得姐姐不够努力。
紧接着来了上山下乡的高潮,热气腾腾,热闹非凡,姐姐自然被裹挟其中,兴奋莫名。
当时已被充军外地,贬到最底层的父亲,也亢奋异常, 还赋诗若干首,赠与姐姐,豪情满怀,慷慨激昂,那真诚,那激情,一点也不逊色胡风的《时间开始了》。我也跟着有了天将降大任于姐姐的感觉,认定姐姐必是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无疑了。
火车站送行,锣鼓喧天,口号震天,满眼大红花,满耳欢声笑语。也有哭的,一眨眼就被革命浪潮吞灭。
下得乡去,常有来信,尽是喜悦,满纸欢颜。几个月后,还寄来照片,长胖了!
再过几个月,来信的味道渐渐变了。知青小组里搞起了互相揭发批判,当然是在上级组织领导下进行的。原来的同学、朋友,一夜之间,皆成仇敌,揭发争先恐后,批判声色俱厉。这对一个还以为能够“随心所欲”的未成年小姑娘来说,不啻是一种毁灭性的心灵摧残!对那些揭发者批判者,又何尝不是摧毁道德、毒化灵魂!
六五年,排行老二的哥哥初中毕业。论成绩,他是班上的尖子。
暑假里,哥哥学校的老师登门了,说要他“一颗红心,两种准备”。老师话音未落,哥哥就冲出去了!
也巧,父亲那几天正好在家(他在外地,一个月把四个星期天挤到一起,回家休息一次),他
通知终于来了,高中自然是没得读的,哥哥进了一所中专。那本是贫苦无告的穷孩子们,梦想吃上国家粮的一条捷径。
开学了,我们学校也迎来上山下乡的热潮。那天晚上,在学校的操场开欢送大会,即将下乡同学们,那般兴高采烈,那般意气风发,放声高唱“一条大道在眼前”。
我坐在密密的人群里,面对灯光灿烂的舞台,面对震耳欲聋的锣鼓,一股黑暗,和对黑暗的恐惧,从心底升起。我埋下头,心中只剩欲哭无泪的伤恸。
六六年,轮到我初中毕业。
离中考还有两三个月,全国人民已经搞起了文化大革命。我们也不例外,天天读那些让人血脉濆张的社论,一时间,群情激昂,摩拳擦掌,磨刀霍霍,准备一场集体的大杀戮。
谁还记得复习功课,谁还在乎考高中!在工作组的领导下,学校党委书记自杀了,老教师剃半边头了,班主任去掏大粪了,……
不久北京传来消息,取消上高中的考试。别人怎么样我不知道,我是着实松了一口气。心中那不时涌动的黑暗和恐惧,悄悄远去。
以后,不断有单位的档案室被砸被抄,我们这才知道,在姐姐的档案里,父亲是“阶级异己分子”,“内控对象”;在哥哥的档案里,父亲却是“右派分子”。而他自五五年被抓入狱,反右时节还在里面吃牢饭呢。
好多人看到自己的档案后,失声痛哭。他们有权愤怒!
两年过去,百般折腾,数番起落,这派那派,都被赶到了同一起跑线上:上山下乡。这是老三届的宿命。
这时我们的身份是:犯了错误的造反派。在清理我们的“学习班”上,工宣队长不无调侃地警告,下乡后,你们可别搞农村包围城市啊!
我们还是带了一台油印机下去了。为什么要带,说不清,可能这是一条理由:它印了差不多两千份杨曦光(小凯)《中国向何处去?》,撒得满长沙都是。在乡下,它只用过一次,为一个不小心烧了山的社员,印了几百份检讨,到处散发张贴。
既然别无选择,再加上一起下乡的都是些最亲近的同学,心境自然和哥哥姐姐不一样,黑暗和恐惧已趋平淡。更多的是新鲜、好奇,还有一点理想主义的改造中国与世界。
临走时,父母正在各自单位被“群众专政”,不得人身自由。是妹妹帮我打点的行装。我却拒绝她们去给我送行…………
那年下乡,我记得没有几位家长能够来送行。
……………………
当年下农村,我想,一千个人就会有一千种不同的心情。
或几个月,或几年,或十几年,或几十年后,再回首农村岁月,一千个知青也会有一千种不同的知青情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