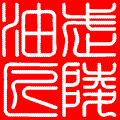(六)
于兆去大队开会回来,通知大家晚上八点召开社员大会,都要按时参加不得迟到。
在这偏僻的水乡,看不到报纸,每天收听大队广播站的新闻节目,成了了解外界的唯一途径,听广播时,大牛总是顺便拨对那只老掉了牙的闹钟 。
今晚开会的会场距知青屋仅二十来米,快八点大牛等三人就到了会场。房主于善听到开会的人到了,忙着放下饭碗,嘴里嚼着饭,拿着火柴过来点亮煤油灯,将灯芯埝得小小的,豆大的灯光喳、喳地蹦跳了几下,发出微弱的光。生产队每次开会,要讲的事用不了半小时,可时间总是拖得很长,都耗费在等人、闲聊和与会无关的争吵中,什么陈芝麻、烂谷子,祖宗十八代的历史旧帐全都翻出来,会议往往拖到午夜才散,可又解决不了什么问题。
农村没有礼拜休息日,天天都要出工,大牛一下子还难适应这早出晚归的农耕生活,感觉极度疲惫,一坐下来就睡着了, 还渐渐发出了均匀的鼾声。小牛、伍晓紧挨着大牛,也趁此机会闭目养神,确实是太累了!队长于兆来到会场,见三个知青在角落里打盹,连忙大声招呼:“嘿!你们来得真早,有七点半了吗?”小牛惊醒了,用胳膊轻轻地推了推哥哥。大牛在朦胧中听到于兆讲的话,睁开了双眼,接上去说:“哦,我出来时看了钟,有八点多了吧。”本想再说点什么,但记起早些日子,因口无遮拦得罪了住户婶娘,马上又打住了。大牛明白,人爱面子,有的人为了顾面子,宁愿听假话、套话、屁话。大牛只得将话题一转:“不过,那钟是只旧货,可能是没对准时间,应该只有七点半吧?害我来得这么早,真误事。”小牛与伍晓不敢出声低头在笑。于兆马上说:“对,不错,你那个钟是‘五·八式’ 的‘跃进牌’ ,肯定不对,现在就是只有七点半!”然而就在这时,大队广播站停止了广播,可是谁都知道,广播是播到到八点半的!
这时,于铁匠、于明、于善、于峰从会场侧门进来。于兆正有点尴尬,
见他们进来,就和他们闲谈起来。过了一阵于万章、于瓦匠、钱师付、万朋,、万权也到了会场。万朋、万权住在中路口,看得出来他俩先到万章家作过短暂的停留后才来的。于兆见又来了人,将话题转到杨李垸、吴家荡生产上的事去了。这时小英和几位大娘、大婶、小媳妇鱼贯而入。其中有几位大牛还是第一次见她们参加社员大会,以前都是她们的男人来,今天不知何故她们也来了。于兆清点了一下人数,人来了不少,但还有几户没来一个代表。他就走到屋檐下大声叫喊:“开会了啊,还有几户没到会,开会了!”这时朱老伯、万杰、万志、王全尚、王全其几个人才慢腾腾地从外边走了进来。
于兆站起来,面对堂屋神龛上贴着的毛主席像,深深地掬了一个躬,从容不迫地转过身来,掏出放在上衣口袋中的语录本,干咳了二声,翻开语录本。这时于善将灯芯埝得大大的,举起煤油灯站到于兆身旁。“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我们的干部要关心每一个战士……。”念完语录于兆开口说:“今天开个社员大会,有的人来得太迟了,个别人还没到,算哒,俺不再等哒”。
大家听了开场白都没什么反应,有的男人在交头结耳,喁喁私语,有的坐下后就闭眼打瞌睡,还有的人在卷烟抽。几位大娘、大婶、小媳妇不像是来开会,而是为节省自家的灯油,借着微弱光亮聚精会神地忙着手中的活,纳鞋底的声音沙、沙作响。
于兆又接着说:“上午俺在大队开了会,回来时快吃中饭了,没有同几个队干部商量,就作主开这个会。”于兆说完这句,抬头望了望王全尚、于峰、于万朋等几个队干部一眼。又说:“上级领导非常关心俺社员群众,拨了一批返销粮,俺队里分到了一千五百斤,怎么个分法?俺个人意见是要发扬民主,采取个人申报,群众评议的办法,做到人人都有口饭吃,不饿肚子。再不能像往年一样靠俺这个当队长的拿出分配办法。”话刚落音,窃窃私语的人停止了讲话,打瞌睡的睁开了双眼,纳鞋底、打毛衣的女人们停下了手中的活,整个会场寂静了,只听到划火柴点烟发出丝、丝的声响。辛辣的烟草味呛得人直咳嗽,会场烟雾弥漫,显得更加昏暗了。人们个个都在心中盘算着。
大牛从其他队社员口中得知,上坪生产队窝里斗出了名,但在瞒产私分这件事上口径一致铁板一块,局外人很难知情。大牛凭直觉也认为队里真正的缺粮户很少,根本没有像他们喊叫的那样严重。早几天,大牛与朱老伯一同收工回来,听他讲:“金牛滩是个产粮区,为了保障粮食生产,政府每年在春耕时节下拨返销粮,价格是议价粮的一半,这个差价是诱人的。”大牛还注意到,近来粮票贩子在这频繁活动收买粮票,每斤粮票可卖二毛钱。一百斤谷指标值十四块钱。朱老伯还给大牛算过一笔帐:积攒十四块钱要在春上喂七、八只大母鸡,日日下蛋不空窝,足足要下一个月的蛋,才能在供销社卖到十几块钱。可是在这一个月中,几只大母鸡需要吃去半担稻谷。大牛开始不明白话中的含意,今天看到开这样的会,开始明白了点什么。于兆见没人发言又补充了一句:“俺队的三个知识青年头年是吃国家粮,这回不跟俺一起分。”话一落音,王全尚的老婆桂枝打破了沉静:“俺没得吃的哒,还要还俺哥哥一百斤谷,他也没得吃哒。俺报三百斤。”大家都知道她哥哥是大队支部书记,怎么会没吃的?她一带头,于万章接着报了三百斤。于兆报了三百斤。于铁匠也报了三百斤……。
大牛一边听着各户的自报数,一边在心中累加,很快自报数已接近四千斤。大牛知道,真正的缺粮户只有于瑞兄妹俩,但是谁也没想到他们。
会场里一阵寂静,大家你看着我,我望着你,谁也不示弱,就这样干耗着。过了一会,于万章打破了寂静:“俺讲二句,俺屋上早就没得米吃哒,先是去别处借,春荒不接都有困难,现在这时节就没得地方借哒,没得法,只好借了知青的米下锅。不信,可以当面问大牛几个。如果没有返销粮,俺就没有米还他们,要是几个知青吊起锅来做钟打(意:没米下锅,只能将锅当做钟敲。)俺可负不起这个责呀!”紧接着几位大娘、大婶也叽叽喳喳跟着讲起来:“俺也借哒青年的米,要是他们没得吃的了,就喊他们去大队要,去公社要,反正俺没得还的。”还有几个也说借了亲戚的谷,朋友的米。总之,个个都有充足的理由要返销粮。
大牛听到这里,才猛然想起前几天万章的老伴言婶娘,清早就端着个大瓦盆站在知青屋门口等着开门借米,后来这几天又来了几户借米的……。原来这场夺粮大战早就开始了!
于兆左手夹着喇叭筒,悠闲地抖动着跷起的二郎腿.不时下意识地掏口袋,摸出火柴做出点烟的潜动作,发现手中的喇叭筒在冒烟,又收起火柴,用右手食指弹掉燃尽的烟灰。听着大家的发言,他不动声色,仿佛早就知道社员们会说些什么,一切都在他的预料之中.
人们的争论还在继续,小牛和伍晓靠在墙上进入了梦乡。再这样“民主” 下去,到天亮也不能解决问题。大家都转而望着于兆,看他怎么办。
其实凭于兆这几年对全队各家各户的了解,怎么分配还不知道吗?只是看到今天开会的阵式不同往年,连进会场都分成了几拔,特别是还来了一群堂客们,来者不善啊!那就更不能轻易表态了。自己的方案要想顺利通过,就不能着急。现在见火候差不多了,他显出付被迫无奈的样子,又看了看每位到会者,才不慌不忙地说出自己的办法:
“今天大家都辛苦了,出了一天的工,会又开到这时节。从申报的数量看,也不是蛮多,都不容易,都有很多困难。俺这个队长没当好家,应当向毛主席他老人家请罪,跟全队社员作检查。大家都缺粮,到这个时节了,都要过这个坎。当干部的就是要让每个人都有碗饭吃,共产党是不允许饿死人的吗!俺有一个不成熟的意见,仅供参考吧。如果不行,只当是写在黑板上的粉笔字,可以随手抹掉不作数。……俺看,还是按人头分配好些。”
于兆讲完,望了望王全尚、于峰、于铁匠几个人,他们马上都表态支持,又不约而同地看着万朋,万朋也发言表示同意。见过了队干部这一关,于兆马上对朱会计说:“明天就按人头分配的方案,造册子上报大队。”
于万章和几个多劳户尽管有不同意见,但也不敢再说什么。这次分粮,于兆又是个大嬴家。万章家六口人,有四个半劳动力,虽不是缺粮户,也没有富余,只是想能争一点是一点,吃不完可以卖议价赚点钱嘛!再说他早就不满于兆的做法了。他们几个队干部都是劳少人多户,所以队里什么好事都按人头来,多劳户总吃亏!可又有什么办法呢?万章根本斗不过他们的。万章是个见过世面的人,被抓过壮丁,在外当过好几年兵,在抵御日冠的战火中,从死人堆里爬了回来。以前他从不信邪,爱提意见、发牢骚,从不把队长们放在眼里。于兆虽装聋作哑不理他,但都一一记在心里。
文革开始后,于兆觉得机会来了。万章这个刺头真可恶,这些年不分场合给自己提意见,讲的话又尖酸、又刻薄,使自己在众人面前颜面丢尽,威风扫地。若能把他当活靶子批斗,既可以杀杀他的锐气,又可以敲山震虎,让队里其他的几个心存不满者老实点。于兆开始琢磨用怎样的罪名,才能将万章揪出来示众。本来可以用“国民党残渣余孽” 这个罪名,可本大队有几个这样的“余孽”,有的人儿子还在大队当干部,这就万万行不通了,弄不好得罪了大队干部,会吃不了兜着走。人们都非常清楚,当年凡被抓丁的,都是无依无靠最贫穷的人家。在有钱能使鬼推磨的社会,金钱能买丁替征,有钱拿钱挡,无钱用命填。万章家穷,只能被抓丁。九死一生归来后,才发现父母双亡,妻子饿死,女儿被别人收养已饿得皮包骨头。如此凄惨的身世,怎么好批斗他呢?
于兆又不甘心,总在寻找机会。有天,无意间听人说万章的老伴以前在地主家当过丫头,马上心生一计:在地主家当丫头,不就是过地主生活吗?说不定还被地主的儿子强奸过!什么强奸,如果母狗不发情,公狗会爬背吗?这种伤风败俗的龌龊事,不斗你还有王法了!马上整材料,揪斗万章的老婆,要整得这婆娘今后无颜见人,谁叫你这婆娘要嫁给这个“刺头”的,活该倒霉。把你婆娘整臭了,才能打掉你的嚣张气焰,让你于万章在这方园几里的土地上夹着尾巴做人,抬不起头来。哈!真是一箭双雕!于兆越想越得意!
不久,由于铁匠组织了个革命战斗队,在生产队召开的批斗大会上,揪出了言婶娘。勒令其交待与地主儿子乱搞的罪行,还准备将其挂破鞋游乡…….。幸亏县革委宣传队在此时进驻平安大队,制止了这荒唐的行为,革命战斗队也随之瓦解。但从此,于万章收敛了许多,再也不给干部提意见,再也不发牢骚了。这个“刺头”终于被拔掉,于兆从此更加巩固了他的地位,上坪生产队再也没人敢和他作对了
其实人都生活在同一个社会中,祸福是相通的,谁有困苦或不幸事,就会触动别人的情感。不说都要将其看成自家的事一样,想方设法去援助,但起码应有同情心。这场批斗会象是一把双刃剑,伤害了别人,其实也伤害了于兆自己,表面看只批斗了某个人,实际上批斗了全队社员群众的心灵,使大家的是非观、羞辱感、恻隐之心通通淡化了。从此,上坪生产队失去了民主,人心更加不齐,生产每况愈下,成了名副其实的“幺儿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