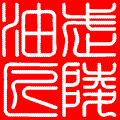(十七)
不久,大牛被调到公社榨油厂工作,
榨油厂是由公社排灌站发展起来的。建站之初,仅有排渍和灌溉任务。后来添置了碾米、粉糠、扎花等设备,开始农副产品加工服务,而且业务繁忙,一天到夜不停机,半夜三更都有人叫门。后来随着国家电力网的扩大,各个大队相继通了电,并也纷纷安装了碾米、粉糠等机械设备,方便了社员群众,大家碾米、粉糠都不去公社加工厂了,为了扭转无人上门的尴尬局面,于是转行办起了榨油厂和榨糖厂。榨糖厂因机械设备和生产技术水平都存在问题,小糖厂又不能综合利用甘蔗渣,成本高造成极大的浪费,而且湖南的土质呈酸性产出的甘蔗胶质过大,榨不出白沙糖。所以不久榨糖厂就停产了,只剩下了榨油厂。湖区盛产菜籽、芝麻,榨油设备又比较昂贵,一般大队购置不起,因此公社榨油厂独家经营,成了骨干企业。
加工厂的职工都是各大队抽上来的农民,每月三十五元工资要交给生产队二十元记工分,参加生产队的年终分配。大牛在加工厂伙房就餐,每顿饭自交大米,另交八分钱菜金,这样大牛每月可以余下七块多钱,个人生活基本稳定下来。到年底生产队还可以分给他一千来斤稻谷、两斤棉花、十几斤油菜籽和数量不少的稻草,还能分到二十多块钱。但分的钱总是不能兑现,只能停留在生产队的个人往来帐本上。后来公社信用社的同志了解到这一情况后,就在每年春耕生产开始时发放的稻谷预购定金中,将大牛应得的年终分配款扣下来交给大牛,同时还要批评队里的人,为什么不给知青兑现年终分配款?生产队的人也自知亏理,从不敢作声。
有一次,小牛与小伍来公社加工厂找大牛,他正巧不在。加工厂的人在与小牛谈话时才知道,她们好多天都没有油吃了。榨油房的会计是个和善的老头,马上拿瓶子灌了两瓶油,要小牛和小伍带回去,等大牛回来付钱。大牛回来后,大伙儿都批评大牛不关心自己的妹妹,她们没油吃了也不知道。加工厂只有一个知青,每月照顾两斤平价油是没有问题的,谁也不会有意见。
人最感不适的天气,莫过于春夏之交的阴霾天。稍活动一下浑身上下就湿漉漉的,很久都不干,叫人心烦。
这时农户的家禽莫名其妙地成群死去,人们知道又闹瘟疫了。对治愈无望的牲猪,有的人家尚存一丝侥幸心理,请兽医打上一针或灌些自熬的草药汤,祈望自家生灵能逃过一劫。结果一觉醒来,头天晚上还有气的牲猪横倒在猪圈中,再也不用喂了。有的人当机立断宰杀一刀放尽污血;这些死去的牲猪处理干净后,称之为“斋猪肉”。“ 斋猪肉”可分两类:宰杀后放尽了污血,肉色发白的,叫做“未倒板”的;僵死在猪舍中,猪皮上带有斑点,肉呈黑红色,腥味特别大的,就叫“倒板”的。“斋猪肉”价格低廉,人们贪图便宜争相购买,毫无顾忌冒险食用,根本不会去想吃了对人有不有害。
有次天气闷热,大多数人去江堤上防汛值班去了。炊事员李伯对大牛几个留守人员说:“俺队里有‘未倒板’的‘斋猪肉’卖,很便宜,俺几个人‘打平伙’好吧?。” 春节归来后吃的都是瓜菜和水煮,很久不知腥味了,还真想吃点肉。但大牛有点害怕,迟疑着不作声,李伯见状反复讲吃“斋猪肉”根本没问题,自己都快六十的人了,不管是怎么死去的家禽牲畜统统都吃过,从没出过状况,身体还蛮好。见李伯信誓旦旦的样子,大牛也就半推半就地答应一块“打平伙”,拿出了该出的份子钱。
中午开饭时李伯端出一大钵热气腾腾的肉,香味四溢,上面盖着一层干红辣椒和大蒜籽,确实非常诱人。大牛还是心有余悸,夹了瓣大蒜籽放进嘴里,像怕食物中毒似的缓缓嚼了会儿,不放心地咽了下去。其他几位伙计,吃得有滋有味挺香的,头也没抬。李伯见大牛还是不敢放心大胆吃,就夹起一大块肥肉放进嘴里,吧叽吧叽嚼着说:“大牛,你看俺老倌子当面吃给你看,几多好吃哦,斯了文会掉武,别等下只剩点汤了。”大牛终于无法挡住这种“美食”的诱惑,打消了疑虑下很心也放纵一回,夹起块肉大口吃了下去,觉得还真是香,接着狼吞虎咽越吃越快,感觉像过年似的“爽”极了!吃完后也确实没有感到不适。这以后再有这种“美食”时,大牛是决不会放过了!
“天晴一把刀,下雨一包糟。”这是水乡村民对乡村道路的描述。冬季的雨雪天,给人出门带来了极大的不便。听长者说:以前遇到这种烦人的天气,出门人就穿“油鞋” ,穿这种鞋其优点是可以防滑,还可减少泥浆水贱到脚后跟上,弄脏小衣(裤子),鞋虽笨重点,可不会比橡胶套鞋差。类似早年长沙人穿的“木屐” 。
大牛在冬日的这种天气,就尽量减少出门,呆在房间坐在床上,用棉被盖住脚,美其名曰“烤被窝火” 。独自一人时可以看书,有人来了可以聊天。有一天,公社管财贸的厚同志途径大牛等人的住处,远远地听到宿舍里的笑声,顺便进屋,见大牛巴掌大的房间挤满了人。“呵,这么多人,好热闹。”大伙见厚同志进来,笑声嘎然而止。还是加榜反映快,叫小赵与老彭挪一挪,在大牛床上挤开条缝,请厚同志坐下。厚同志笑着说:“怎么都不讲话了?刚才还听到里面打哈哈,好热闹,什么喜事,我也分享一下。”大家刚才只是在打无聊的嘴巴仗,“伙喜儿”(开玩笑)。经厚同志这么一问,都不知怎么回答,沉默了一会,厚同志见大家还有些拘谨,就打破僵局问大牛说:“这是你睡的床?”大牛点点头“是。”厚同志摸了摸被子,马上说:“哟,这么薄的被子,小伙子啊,过两天是冬至,该换大被子了,都什么时候了,还盖春秋被。”大牛不以为然;“我就这么一床‘秋冬被’ 盖了十几年了,和它有着深厚的革命情谊呢。队里每年才分斤多棉花,攒几年也不够弹床棉絮的。不过我是久经‘冻练’ 的老战士了。”厚同志见大牛还说调皮话,笑着说:“不行,这么冷的天,冻病了怎么办?哎!早知道就好了,公社今年的棉絮刚分配完。这样吧,明天我去问问供销社,看有没有剩余的,只要有一定帮你弄一床。”大牛因工作关系与厚同志接触较多,比较熟悉,厚同志平易近人,没有干部架子,因此在他面前不会感到拘束,偶尔还跟他开开玩笑,厚同志见到大牛也喜欢聊上几句。
在大牛的记忆中,这床棉絮是祖母在世时用的,老人去世后,正在上小学的大牛,就睡在了祖母床上,盖了这床棉被。它陪伴大牛读完小学、初中、又带着上高中寄宿,渡过了整个青少年时代。
第二天大牛正在上班,厚同志手上拿着张批条,满面笑容地又到了加工厂,对大牛说:“你的运气好,供销社还有棉絮,快拿批条去买。”说完将手中的批条递给了大牛,又说:“你知道吧,湖风吹老少年郎,冬天湖区比长沙要冷多了,小伙子,要买就买床重点的,晚上睡得暖和些。”大牛拿着批条很高兴,对厚同志谢了又谢。
其实当时下乡时,工宣队的人见大牛的被子又硬又薄,给了一张棉絮购买券,但是,大牛的父亲关在“牛棚” 里并扣发了工资,哪有钱买呢?他拿着工宣队开的的证明到父亲单位借钱,那位领导瞥了大牛一眼,抽出根大前门香烟点燃,吸了一口,给大牛上了堂政冶课:
“响应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号召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对你来讲是非常必要的,但困难谁都会有。听说你原来在学校寄宿,应当有被子盖啊,可能旧了点,但还可以用吗!贫下中农几个人才合盖床被子,你一个人有一床,这就很不错了,困难,可以去克服吗。你要注意不能脱离人民群众,艰苦扑素的作风不能丢啊,。”就这样,抽大前门香烟的革命干部打着官腔,硬是没批钱给大牛。
大牛没法子,只能将旧棉絮晒了晒,掸去灰尘。母亲含着热泪将被里洗干净补好。大牛带着这棉被来到了太平公社,一晃又渡过两个数九寒冬了。在严寒的夜晚,在四面透风的草棚里,正如厚同志说的那样,大牛从没睡暖和过,早上起床全身冰凉。抹去似清水的鼻涕,再使劲跺跺脚,才逐渐缓过劲来。也许是祖母的在天之灵保佑着大牛吧,也许是久经“冻炼”抵抗力强吧,大牛居然从没被冻病过!
买回厚同志批给的棉絮,大牛心里无比温暖,他觉得隆冬即将过去,春天就要到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