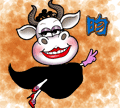每篇文章或一本书都有个标题,在图书馆称之为“题名”。西方图书馆在编目录时是的著者放在首行。而中国不同,是以“题名”放在目录最上一行,称为“标目”。这从一个侧面反应中国人把“题名”看得比著者名重要。我也有这个毛病,有时读完一本书,只记得书名,是哪个人写的浑然不晓。
《靖县知青文集》收录了百余篇文章,我深知题名的重要,所有题名都是作者前思后想的结晶,可是我忍不住也就动笔改了几个题名。
眯子兄写的《被抓》,当他和另一位知青被五花大绑投入“监狱”时,仍高声唱着“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汉字是由图画演变过来的,保留了图案的痕迹。形容坐牢用“囚”字表达。如同人被关进一个笼子。我将眯子兄的这篇文章的题名改成《囚》,我觉得更形象,更简洁。
良良哥有一篇《屙野屎》,讲的是两位高度近视的知青,一男一女,为了使自己“劳动人民化”,他们取了眼镜。男知青蹬在野外方便时,这位女知青没看清实情,走上前去与之讨论另一个人入团问题。男知青羞愧难当,女知青浑然不觉。文章内容有时代特点,只是我觉得题名不雅,改成了《尴尬》。
哈免的《吃杨梅》,写出了女知青潇洒中带点调皮和山里人的宽容与大度。主人翁伸长着颈根,吞咽着蜜甜的桐木杨梅,果汁流出来,衣襟染成了红色,好像在欠我们,让读者边看边吞口水。这就是女知青当年的“吃象”。我不想影响女知青的“光辉形象”,把题名改成《品杨梅》。
每天上班,利用半小时乘坐公共汽车的时间思索。头天夜里编辑的文章在大脑萦绕,此时此刻我目空一切。题名如何更加贴切地反应文章内容,如何做到更加简练。一有顿悟,脸上泛出笑容,旁边的乘客以为碰到了“神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