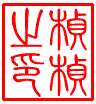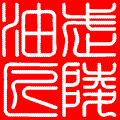加工出口鱼
有一年冬季开湖,我们渔场的大架网一网就起了一万多斤雄鱼。这批鱼个头均匀,条条都在10斤左右,把公社水产部主任乐坏了,他正愁完不成出口鱼的任务呢。于是立即下令,招来了以他老婆为首的加工队伍—一群年龄在40上下的大婶们,在院子里扯上大灯泡,准备挑灯夜战。
当时我和回乡知青小爱受渔场安排,正奔跑于各湖荡间取鱼的脑垂体,以备来年种鱼繁殖时催情之用,也正愁完不成任务呢。这下好了,只要守定这批鱼,不就什么都有了?
事不宜迟,我们立即赶到公社水产部,这时第一批鱼已经运到了。我看着堆成小山一样的鱼兴奋不已,小爱却叫我不要高兴得太早了,“会累死去咧!”她说。小爱个头较矮,心眼却特多,讲话时一双大眼睛眨啊眨的,仿佛有无数个主意会从眼睛里眨出来,比我这高个子能干得多。果然,她在院子里溜了一圈,不知从哪儿借到两只小板凳,她递了只给我,“不搞个凳子坐,这一晚难熬啊。”
水产部主任作了一番动员,无非是加工出口鱼是支援世界革命啊,是光荣的政治任务一定要完成啊……可那些大婶们都顾不上听,忙着磨起她们随身携带的杀鱼刀来,这种刀前面带尖,刀刃呈圆弧型,厚重沉手。刀磨好了,她们扎上围腰,带上一种橡胶袖套,麻利地操作起来。
我和小爱将凳子放在她们中间,这样前后左右的鱼我们都可以够着。取鱼的脑垂体比较简单,鱼脑袋被劈开后,只要把里面的脑髓扒开,在鱼头骨正中可以看见一绿豆大小的白色物体,这就是脑垂体了,用挖耳勺探进去将它挖出来,再浸泡在装有酒精的小瓶子里,头道工序就算完成。问题是脑垂体挖出后必须完整无缺,所以挖它时必须小心翼翼,不然挖烂了就没用了。
大婶们动作很快,我们也停不下手,她们加工一条我们就得挖一条。但忙里偷闲,好奇心促使我不断地向最近的那位大婶问这问那,她可能见我是知青吧,一边回答一边示范,我渐渐地搞清了,加工出口鱼技术要求十分严格,特别是剖鱼这一环节,多大的鱼划几个刀口,都有严格规定。
首先,刀口从背上切下去,要笔直的,不能歪斜,在距离鱼尾两寸多的地方成直角转弯开向肚皮,鱼头也要在正中劈下去,不能歪斜。这么大的鱼头,要达到这个要求,谈何容易。可大婶们熟练地摆弄着那些鱼,碰上太大的就一人掌刀,一人用根木棍敲刀背,条条鱼的刀口都齐斩斩的非常漂亮。开膛后,鱼杂要挖出来,鱼鳃要掏干净,然后在有脊锥骨的这一边划三个刀口:沿着离脊椎骨约
由于是第一次参与加工出口鱼,我的兴致很高,一会帮大婶敲木棒切鱼头,一会又在鱼杂里翻检那些鱼心、鱼肝、鱼泡什么的,放到大婶带的一个大钵子里。我问了一下,这些东西要出钱买,一毛钱一斤,非常便宜。这是大婶们的专利,外面人买不到,哈,这个特权可不小啊! 小爱见我不停地折腾,告诫我保持体力,“还有一晚呢,你等下莫喊天啦!”我也有点累了,就在小板凳上坐下来,老老实实地挖脑垂体。
夜渐渐深了,凛冽的湖风一阵紧似一阵,院子的围墙,根本挡不住肆虐的北风,我们虽然都穿了棉衣棉裤,脑袋上还包着围巾,还是觉得寒冷刺骨,特别是一双手,糊满了鱼血、鱼涎,只能露在外面冻着,早已麻木肿痛不听使唤。清鼻涕接连不断地淌下,只好时不时用衣袖噌一下了事。双脚也开始酸胀疼痛。这时我才明白小爱见了鱼为什么高兴不起来了,这还真是个折磨人的活啊。
我咬牙坚持着干,机械、吃力地把那些大鱼拖过来,扒开脑髓、挖垂体,一条又一条。看看那堆鱼,还有不少。后来眼皮也开始打起架来。小爱见我有点不行了,就叫我起身活动一下,去把手洗干净,揣起来暖和暖和。
我转了一圈,找水洗手时,发现院子的另一边是一溜几个大水池,那些加完头道工序的鱼都被浸泡在水池里,几个大婶拿着剪刀,把泡得发白的鱼拖上来继续修剪,这想必是第二道工序了吧?问了问一位大婶,才知修剪完了还要换水继续泡,要泡得直至鱼肉发白水变清,才上盐腌制,腌完第一次还要再泡一道水,然后再腌几次,直到把鱼提起来不滴水了,才算完工,才能装运出口。
我很奇怪,不是出口鱼吗?我怎么听着这鱼最后变成咸鱼干了?要不是出口鱼,我们渔场的大雄鱼岂不惜哉!
带着满腹疑问回到这边,忍不住和小爱说起来,水产部主任的老婆听到我们的议论,赶紧走过来制止我们“莫乱讲咧,这鱼真的是要出口的,”她看了看四周,压低声音“听说是罗马尼亚,那些外国佬,都不煮了,吃生的呢!”
哦,这就对了,主任开始不就讲了是支援世界革命吗?我怎么连这个道理都不懂呢?虽然是咸鱼干,也是中国人民口里省下来的啊!我顿时为我们伟大的国际主义精神感到无比自豪!并且如此说来,大雄鱼们则应是壮哉了!
天蒙蒙亮时,鱼终于剖完了。带着满身的疲惫和血污,我和小爱慢慢往回走,小爱叹口长气“唉,总算搞完了!”而我一边走一边还在想着咸鱼干和世界革命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