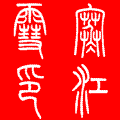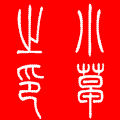我小学,中学都与沙阳同学。
我小学在城南天心阁完小读书,三,四年级时沙阳从黄兴南路小学转入我校,不同班。彼此认识,那时他个头不高,夏天额头上长了几个很大的疱疖,其貌不扬,但双眸里透满灵气。初中一同考入妙高峰上的第十七中学,我38班,他42班,教他的班主任姓周,管教甚严,不能与其他班同学玩耍。周头上长了个小脂肪瘤,俄语“仔”的读音为“史拉非亚”,同学恨他严厉,辱之,呼以此小名。那时,沙阳课余打蓝球苯拙的投蓝动作,给我留下深刻印象。还有,他学某体育老师示范投蓝,三投不正仍不失老师尊严的样子惟妙惟肖,他给老师画象叫人捧腹!那时就展现了那种幽默才华和大家愿意听他玩笑的凝聚力。
高中我们有幸都在师院附中61班,同一出身,同被压在唯成份论之下的我俩,感情更加密切,乃至以后一同搞战斗队,一同下放,历经各种磨练,结下了深厚的情谊.我们几十年来从未断过联系。
他出身在教师世家:父亲是语文教师,有深厚的文学根底,历史人物,文章及典故信手拈来,描绘得有声有色,如同亲身经历一般。他父亲非凡的记忆力,逗笑的描述口才,几尽完美地遗传给了沙阳。加上母亲的豁达心胸,遇事沉着,不惧外压的性格都在沙阳身上烙上深深的印痕。在附中,他是美术组长,如果没记错的话,第一个公开展出的人物素描头像的原型就是我。1967年为保卫国庆“安全”,我家一半以上的人被当作牛鬼蛇神关押在白沙街小学,是他奔走各地实施营救。
下放农村后,我们情同手足。先进知青组的发言、巡回演讲、重大时期写作文字,都是他“一碗饭”;知青茅草棚的落成大门的对联,也是他一气呵成。下放第一年,他就小有名气,可惜和我一样,招工回城的光环一直不肯降到我们“优秀知青”的头上。无非是那"黑七类"子弟没人接收,再加上“公社管知青党委想要他一顶解放军冬帽,他死活不给,大队管知青的妇女主任借他几尺布条子,他想方设法去讨要”的傻冒表现,一直让我们找不到好运。但他有这些爱好后,也给他带来“娄活”。当记工员,每天在第四歇工望不到收工时,他可在路上吊一下,晚上扯夜秧时,他可伸直背去呵斥人家“毛巴砣”(秧冒洗干净)而不给验收。“农业学大寨”后加个句号的大堤石灰标语,他可以花60—70分工,一个星期不换地方地轻松,谁也不敢在政治问题呸他浪费工。使我这扮禾桶长,插秧组长望尘莫及。晚上偷毛桃、看牛婆生崽、替猪婆接生、捉青蛙、撮晒死的鱼嫰、检闹(毒)死的鱼、到湖田守草,他样样有兴趣。口口声声最喜欢恰闹(毒)死的鱼。天热穿毛笔几当当小衣(内短裤),等等,都在沙阳大队留下笑柄。
我一生,结婚,做屋,生崽,儿女结婚办事,包括孙女取名,都有他的参与,我们俩家生活和工作的基本动向,相互都十分清楚。是一世难得的知己。和他度过生命的主要阶段。留下的回忆太多太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