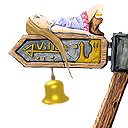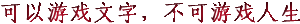山湾湾里的人家 (知青生活扎记)
.
这是一个典型的山里人.宽阔的脸膛,浓厚的眉毛.个头不高,却是十分的壮实,用熊腰虎背来形容,想来不会过头.两条粗壮的腿,肌肉十分发达.那是常年在山林中行走劳作的象征.徜开着衣襟,露出宽阔的胸怀,皮肤呈古铜色,在阳光之下闪闪放光.
兴许他赶闹子回到山里,忽然在我们那所小学校停了片刻.那时我正在上课,不经意望了下窗外,就见他远远地立在那里,盯住教室出神.
“这人是谁呢?”我想。下了课,本想和他攀谈两句,但他一见学生从教室里涌出,便急匆匆地走了。邱大爹的儿子黑皮揣测出我的心思,连忙说,他是周大宝和周小宝的爹。既然这样,在这篇文章里,我就称他为老周吧。
他的那两个儿子大宝和小宝,和别的山里娃娃很有些不尽相同。一般的山里娃娃,上课的时候,倒是蛮老实的。但一下了课,那就个个都成了飞天蜈蚣。要说有多淘气,那就有多淘气,为了争夺一只永远也充不足气的篮球,他们会滚成一堆,爬起来个个都成了泥猴.要不然,他们就会在那条小溪里打起水仗.……而这两个小家伙,却从不参与这种淘气蛋们的游戏,只在一旁静静地观赏.尤其是那个小宝,竟然常常依偎在他哥哥的怀里,看得高兴了,只悄然无声的一笑.
这哪像是山里的娃崽哟,比山里的女娃崽还腼腆还温柔呵.
那小宝,是班上最小的学生了.只有六岁.山里的学生上学都要走山路,而且是翻山越岭,涉水过桥.能到这山的腹地来读书的学生,大都在七八岁以上.我纳闷了,开学的那天,我问过大队支书,这小宝才这么点大,他家里人也放心么?大队支书只是笑了笑,却没有正面回答我的问话.
每次我给一年级上课的时候,那个小家伙似乎是很认真听的,他总是托着腮帮子,睁大眼睛望着我.只是,他太爱分神了,那怕有一只小蝴蝶从窗外飞过,他也会目不转睛地盯住窗口,老半天回不过神来.我只好用教课书轻轻地拍一下他的脑壳.一个生字,教了几遍,他也能认出来,可是,你将那字放大一倍,他却是了“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了.让你哭笑不得呢.
我不会责怪他的,他还太小.我就见过有山里娃崽,七八岁了,还时不时依偎在他娘的怀里,吮吸着乳头.这个小家伙,在家里是不是也是这样的呢?
我总想和他谈谈话,然而总不成功.他一见我叫他,就躲藏在他哥哥身子后面了,只露出一双黑乎乎亮晶晶的眼睛,怯生生地望着我.我也就只好作罢了.
也许是他哥儿俩觉得我还算好吧,一天,老周特地来学校看望我.他先让我卷了一支他带来的旱烟丝,见我抽着了,并且深深地吸进了肺腑,就说:烟烈着呢,别呛着了.
我说:这烟味道真好.
他说:是用桐油枯种的呢.
的确,山里的叶子烟,烈是烈,但烟味十分纯正.那是山外那用人粪或是猪牛粪种的叶子烟没法比拟的.
我们抽着烟,坐在草地上,闲谈了几句.老周说:郭先生(注:瑶山里的人称教书的人为先生),我的娃崽要是不听话,你就给我打,我不怪你的.我说:老周哟,这可使不得呵.你不怪我,公社文教组也会把我给撤了.我可是舍不得你们这瑶山呵.那老周听了,连忙说:是这样,是这样.
这次和他谈话没几天,我那窗台上,就有人给放了一大把上好的旱烟叶子.那当然是老周悄悄地放的.后来又有一次---那大概是六月里,老周出山经过我这里,悄悄地将一包东西放在我的窗口,那时我正在上课,他只向我打了一个手势,就匆匆忙忙地走了。下课了,我将那包儿打开一看,是一包嫩生生的鲜玉米,个个一般大小,还散发着清香散发着甜味。土生和黑皮连忙告诉我:这是五月苞,可好吃了。晚上我就啃着这些五月苞,品味它的香甜,心中却在想:没想到这个豪爽的山里汉子,心却如此……如此的妇人心肠……
我只去过老周家一次。一次放学的时候,我随学生一道出门。本想只在山道上走动走动,却走到了那座木桥,那通向双江口的木桥。在那儿和双江口的学生分了手,转过身子,进了老周家的那道山湾子里。我真的是大开眼界了。那山湾里简直就像是个世外桃园,一个童话般的天地。一块平展展的田园,种着玉米荞麦,还有几丘水田。一条小山溪在那田园中穿过,静静地晃荡着山林的倒影。田园的四周,环绕着山林。远远的那靠山边的地方,是一幢小木楼,木楼之前是一片菜地。一排用树枝和方竹(注:竹杆为方形,是那山中的特色植物)编织的栅栏,栅栏之上,凉着几件衣物,清一色的黑布衣。山湾子里空无一人。就连刚放学回家的那两个小家伙也不见了影子。但那木楼之前,却有一条赶山狗,笔直地蹲在屋前。我有些胆怯了,不敢往前走动。只见那狗,对我也不在意,于是,便选了一个平整树墩,坐了下下来,点起了烟。
我没有表,估摸着已是五点多了吧?而在这山林中,天色却已近晚了。我站起身子,准备打道回府。正在此时,那两个小家伙却呼唤着从木楼后边的山坡跑了下来。他们一下子就发现了我,大吃了一惊,急忙停住了脚步,怯生生望着我。刚才那股子顽皮之态,不知怎么地又不见了。原来他们在家里,也是很活跃的呵!我笑了笑,向他们挥挥手,就走了。
晚上批过作业,我又到老邱家去扯闲话了。我说起了山湾湾里的那种感受。老邱说:不容易呵,那老周又当妈又当爹的,真的就将娃崽拉扯大了。
我连忙问:这老周怎么会没有婆娘?
老邱说:没有婆娘哪来的崽哟?他婆娘去了,就在生小娃崽的那天,流血过多,就走了……
原来是这样。我想起了那栅栏上全是黑布衣,就没有一件瑶家女人常常穿的那种绣花的衣。我想起了那天我问过大队支书,这小宝才这么点大,他家里人也放心么?大队支书却没有正面给我一个回答……原来,他是将小宝放在学校里,让我看管他呀!这远比把他扔在家中没有人照理要好多啦!
“这老周怎么还没有另找婆娘呀?”我问。
老邱说:“还不是怕后娘对娃崽不好?他不敢娶呵。”
我没有再问下去了。一个精壮的山里的男子汉,谁不想有一个婆娘过日子,可他却为了怕娃崽受冷落,不再续弦了。我为这山里的男子水般的柔肠,感动了。
后来,一封匿名信寄到了县教委,说是瑶山不能由一个出身不好的知青来当老师。县里将这封信转到公社。公社文教组只好将我调到山外的源头小学。我自信在瑶山的那一年,成绩还是可圈可点的。写那封信的人意图我还是可以揣测到的,无非是眼红罢了。那山中的工分值是一元五角钱一天呵。
在源头教了一年,我就去了源口水库。1978年的7月,妻子在长沙为我办好了病退。回长沙的那前的一天下午,我去了一次瑶山,又一次走进了那山湾湾里。山里没有人,我仍旧在那个树墩上坐了一会儿。我望见,老周家的那屋前的栅栏上,依然没有瑶家女人的花布衫……
我真希望有一个好心的女人,能走进这个山湾湾里,为这个山湾湾里的人家,带来温馨,带来甜蜜的生活气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