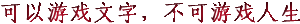我写下“我的朋友”几个字时,那种释怀的感觉让我不得不停下来,不得不喝一点啤酒来配合我的高兴。三十八年了,我无数次的想到这个人——曾建,我的同学,童年的玩伴,想到我施与他的种种伤害。每想一次都让我负疚增加一点,年龄越大越这样。我想过向他道歉,但想不出怎样的语言才能表达我的心情,于是我希望他有什么难处我能够助他一次,但也没找到这样的机会。
这次鲁小兵回国发起三十多年来第一次小学同学聚会,让现在天各一方的我和他有理由重聚。我想到他对我的怨恨的可能,想到他不想见到我的想法的可能,终于拨通了他的电话:“曾建么?我是梁欣…”我作了几十年准备的致歉的话还没说出一句,就被他欣喜的话语挡得永远没有了说出的可能“梁欣,你现在哪?你好啵?明天你一定要来,我最想看见的就是你了。”“……我……”我试图让他知道我的负疚,又被他快活的声音堵了回去“什么都别说了,明天见面,好朋友,几十年没见面了……”他还说了许多话,但我只因为这一句“好朋友”折腾了几乎一夜。
我和曾建算是发小,还没上小学就玩在一起。在伢子群里,我也算是一个说得起话的,胆子不小,点子又多,因此走到哪,总有一群大小伢子跟在后头,曾建是其中一个,虽然不算“铁杆”,但也次次尾随,言听计从。
文革一起,我的父母被“专政”了,我的“威信”好像也降低了,一些伙伴由于父母与我父母划清界限也跟我少了往来,像曾建,他的爸爸是造反派,当然不会让他跟我这“狗崽子”混。但我俩之间真正的过节是从一件事开始的。
这天早晨,一群被专政人员去劳动从我们宿舍经过,我看到父亲走在其中,他没像别人那样沮丧,很坦然地走着。这种神态可能很让那个造反派的看守不痛快,仿佛很不能衬托他小人得志,颐指气使的派头。只见他提着皮带朝我父亲走去,“梁峥(老实说,当时听别人这样直呼父亲的名字我都麻木了,小孩子都可以这样,尽管这之前我父亲一直被人恭恭敬敬地称为‘梁工’),老实点!”断喝声中,还把皮带当空一挥,甩得生响,好像要落在父亲的肩上。一个年轻点的看守好像得到命令一样,走上去把父亲的头使劲按了下去。我再也看不下去,血直往头上涌,我冲了过去…一个过路的叔叔拖住了我,那一瞬间,有两个人的眼光我终生难忘,一是父亲制止我的眼光,一如父亲平时的深沉和慈爱;再就是那个中年看守惊惧的眼神,我认出了:他是曾建的爸爸。
这一天我都在想着爸爸。晚上礼堂里还灯火通明,听说是有人在挨斗,我便关照妹妹睡下,朝礼堂跑去。在跪着的几个人中,我果然看见了爸爸!他头上戴着纸糊的高帽子,可能由于跪得太久腰吃不住,用手撑在地上。我的心开始流血,我知道不能莽撞了,莽撞只能让我的父母更受罪。这时,那个人,姓曾的,又提着皮带走向父亲,不知说了句什么,只见父亲把手提起,直起身子。由于没了手撑的帮忙,父亲的身子有些摇晃,。他从口袋里掏出本子和笔,就这么直跪着写起字来。我明白了,这姓曾的是在借“做笔记”升级对我父亲的整治呢。由于改变了姿势,父亲头上的高帽子有点向后倾倒。上午那个狐假虎威,按我父亲头的年轻看守上前去使劲一按,帽子又正立起来,但帽檐上的铁丝把父亲的额头重重的划了个口子,鲜血流了下来……一声哭叫在我的身后响起,是我的妹妹,我赶快拖起她离开了会场.兄妹俩抱头狠哭了一场。从此我再也没去看过父母挨斗,但在心里把曾建的爸爸恨得不共戴天了!我暗暗的记住他整我父母的次数。
六八年,曾建与我一起下放,分在一个生产队。我想老天眼没瞎,你老子造的孽你做儿子来偿还吧!于是我开始在他身上实施我的“复仇”:每天都要找碴与他打架,每次都下狠劲揍他。他不是我的对手,,常常是鼻青脸肿的。每次打完我都威胁他,如果告诉他那个看守爸爸,我就要他残废。到后来他都不还手了,听凭我欺负,直到我下不了手了。不但如此,他还主动与我和好,帮我打洗脚水之类。那一段时光我现在想来他是生活得如在地狱的。我有些觉得自己做过了,但一想到父母所受的屈辱,心肠便硬了起来。后来听说他回家后多次跪着求他父亲别再整我父母。我才醒悟到他其实是无辜的。但年轻气盛的我当时是不会想到给他的伤害有多大的。
我再见他时,还是忍不住提起这事,他淡然说:“这事放在谁身上都过不得坳,我伤在皮肉,你伤在心里。我早忘了这事,你这么多年还放在心里熬,你被伤得重些。”他反而劝我说:“莫想这事了,都过去了。朋友之间,不打不成交啊!”
我跟我的一个挚友说起这事,她说:“你们俩的心灵都成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