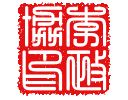[日期:2007-06-07]来源:郴州日报 作者:本版所有稿件均由本报记者钟媛提供
人的一生就像一场考试
在无休止的竞争中
我们蹉跎过、挣扎过、拼搏过
最终变得坚强而成熟
多年以后,当我们回首一生
那些考试就像生命中的年轮
依旧如此清晰
也许只要笑对人生
我们就能傲视输赢
Ⅰ:在懵懂茫然中经历人生转折点
受访对象:
高飞,1957年出生,参加高考前为下放知青;1977年考入湖南省衡阳医学院,毕业后一直在卫生系统工作,现任嘉禾县药监局局长。
年近半百的高飞,看起来要比实际年龄年轻。说起当年那场改变命运的考试,他大有感慨,但也并不掩饰当时的懵懂与茫然。
1972年,高中毕业的高飞被下放到嘉禾县园艺厂。1977年7月左右听到逐渐蔓延开来的恢复高考的消息时,他并没有什么很特别的感觉,甚至对高考有一点漠视。
“当时长期受‘读书无用论’的教化,我几乎想不到读书和外面的世界对自己有什么影响,只想抓紧时间把手头上的事情做好,并且响应号召‘扎根农村一辈子’!”
不过最后高飞还是报名参加了高考。一是因为一直成绩优异的他,看到许多成绩不如他的人都报了名,心里有些不服气;另一方面,则只不过是出于对高考的好奇。
但让高飞感到头痛的是,当时不仅没有补习班,就连考试的范围和内容都没有划定,也没有任何参考资料。在他的记忆里,大家都是四处寻找能够找到的各种书籍来“临时抱佛脚”,“抓到什么就复习什么” 。
而高飞相对来说比较幸运——他所住的院子里,有一位60年代初期的中专毕业生保留了一套相对完整的教材,并爽快地把书送给了他;他的表姐夫是文革前的大学生,自告奋勇为他补习化学;另外,他还得以在另一位高级知识分子的辅导下补习数学。
“因为完全不知道要考什么以及考试的难度,加上复习时间也已经很紧,帮我补习的人只能根据他们以往的经验,挑选其中的重点、要点来为我讲解。”回忆起往事,高飞突然有些忍俊不禁。
原来,当时为高飞补习数学的高级知分子担心出题过深,所以第一天就抓紧时间为他讲解微积分。看到试卷时,高飞才发现只有两道参考题涉及到了微积分的内容,其他都是一些比较基础的问题。于是就出现了这样一个让人啼笑皆非的现象:两道难度较大的微积分参考题,高飞拿了满分;前面那些基础而相对简单的题目,他却考得很不理想。
而在当年,对高考的政策和作用感到懵懂茫然的,并不仅仅是高飞一人。高飞告诉我们,那时很多人都不确定高考录取的标准到底是什么,对知识考核的重视仍然远远不如对政治思想的要求。以至于在他下放的园艺厂里最早收到录取通知的是一名被认为“调皮捣蛋”的青年时,园艺厂副厂长极为愤怒,连声抱怨那次高考“太不像话”,“怎么厂里的党员没有被录取,倒把这个捣蛋的‘阶级敌人’录取上了!”
高飞本人在等通知的那段时间里,却毫无压力感。1978年4月接到衡阳医学院的录取通知书时,他竟然还着实犹豫了一番!
面对记者的惊讶,高飞解释道:“那时知识分子没地位,家里人看到身边担任领导职务都不是知识分子,怕我去读了书之后,反而耽误前途。”
高飞的父母都是解放前的初中生,深深了解知识的宝贵和重要,因此一再坚持和鼓励他去读大学。想到读大学终究是改变人生的一个机会,高飞还是踏上了求学之路。
“现在想来,真的很庆幸自己去读了大学!”追忆往昔,高飞深有感触。“不读大学,不知道自己究竟有多无知,也不会随之养成求知、自学的自觉性,更不会树立起明确的人生目标和奋斗方向,很可能就碌碌无为地过完一生了。”
毕业后回到嘉禾工作的高飞职务不断升迁,努力学习、积极求知的习惯则一直没有改变。现在,临近知命之年的他,仍然乐于多方面接触新信息和新事物,并从中汲取新的知识,不断地充实和提高着自我。
记者手记:
1977年中旬,恢复高考的消息开始慢慢传播开来。但即使是在举办高考的消息被确定的时候,仍有相当一部分人对高考的意义和可能带来的各方面转变不甚了解。具体到考试的内容、范围、形式等等,大家更是毫无头绪。在没有统一教材、没有考试大纲、没有补习班的情况下,报名参加高考的人们只能凭着各自的揣测,几乎有些盲目地进行复习。
这样的情况并没有持续多久。据了解,1977年冬季高考结束的第二年,各地逐渐出现了由各学校组织开办的高考补习班和下乡辅导班,人们对高考的认识也很快全面和深入起来,学知识、重文化的风气由此得到了复兴。可以说,1977年高考的恢复,对扭转人们对知识文化的态度,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Ⅱ:“历史不清白”曾让他失去上大学的机会
受访对象:
曹柏全,1957年出生,参加高考前为下放知青一员,曾任民办教师;1977年参加高考,上线,但因家庭历史问题未被录取;后持续2年参加高考,1979年考入耒阳师范;毕业后在教育系统工作多年,现为嘉禾县委党校副主任科员。
说1977年的那次高考,曹柏全的言语之中仍旧充满了遗憾。那年,下放到嘉禾县普满公社向阳茶场的他,因为高中成绩优秀,已被调到村小学做民办老师,远离了知青点,也无法深入了解当时的政治形式。
曹柏全接到恢复高考的消息时,已是1977年9月。考虑到机会难得,他还是抓紧时间报了名,并利用一切可利用的条件,开始了复习。
由于基础知识扎实,虽然有着资料缺乏、知识陈旧等实际困难,曹柏全仍然考到了超出当年高考录取分数线的好成绩。接下来,他便满怀欣喜地等待着录取通知书的到来。可是时间一天天过去,许多分数低于他的人都已经收到了录取通知,他却迟迟没有等到属于他的录取书。看着其他人一个接一个地背起行囊奔赴大学校园,不明就里的他困惑低落之余,不免有些心灰意冷。
这时,向阳茶场的场长知道了曹柏全的事情,并向他详细了解过他的报考情况之后,方才找到了原因所在。
原来,填报考表时,曹柏全不知道“社会关系”一栏应该如何填写,在场老师便提醒他应该写明“父母家人是做什么的,有没有亲属下落不明,有没有亲属在台湾”。于是,毫无社会经验的他,在填写了矿工出身的父亲和贫农出身的母亲的情况之后,又老老实实地写明——“爷爷曾被国民党抓壮丁带走,至今下落不明,不知道有没有去台湾”!
就是这样一句话,使得曹柏全未能通过“政审”一关,痛失了上大学的机会。曹柏全后悔不迭,却也无可奈何。但知道了结症所在,好歹也让曹柏全恢复了了信心。1978年7月,他再次参加了正式恢复的夏季高考,刻意回避了自己的“历史问题”,却不料以2分之差失利于考场。
1979年,不甘心的曹柏全又一次参加了高考。这次,他专门请了假,到嘉禾一中开办的复习班专心补习了两个月。
接到耒阳师范学校的录取通知时,曹柏全已经回到父亲工作的煤矿做了机电工,可以拿到每个月28块钱的工资。此时的他看到录取通知时,心里已经没有了往日的激动,第一感觉反而是——“不想去!”
为什么不想去?因为他不愿意做老师;因为在当时,老师的地位甚至不如一个供销社的营业员。“当时很想去铁道学院、农业学院、煤炭学院这些学校,从来没有想过去读师范、做老师。”
最后他还是去了,没有文化的父母说了句再朴实不过的话——“读书总是有用的”,深深地触动了他,于是他走进了耒阳师范学校。
如今回想起当时的犹豫,曹柏全忍不住大笑。他感叹到:“还是出来读书了好啊!当时如果不去读书,而是继续在煤矿里工作,现在就只能面临经受改制、下岗的命运了!”
记者手记:
1977年高考,并没有对考生的出身、家庭背景作出强制要求,这相对于“仍然以阶级斗争为主”的文革时代来说,是一个不小的进步,也给了无数“出身不好”、“社会关系复杂”、“历史不清白”的人寻求新出路的希望。
然而,在恢复高考第一年的录取过程中,仍有一些时代痕迹一时无法抹去。那些在今天看来可笑、怪异、不可理解的原因,却能让许多人的梦想瞬间破灭,让他们一生的命运随之发生更加预想不到的转变。这些都是那个年代特有的烙印,恐怕,也是如今我们应该仔细品味的地方。
Ⅲ:高考打造出的农学专家
受访对象:
李国彪,临武人,1956年底出生,参加高考前为下放知青一员,曾任供销社代销员;1977年考入湖南农学院,毕业后回郴工作,现任郴州农业局副局长;2004年应联合国邀请前往孟加拉实施“粮食安全特别计划”,担任专家组大组长。
李国彪的儿子,是今年参加高考的应届考生。父子两代人,时隔30年,在一个共同的战场上咬牙以搏,双方的感受却大不一样。
李国彪说,他当年的压力,远没有儿子现在所承受的大。
当年压力不大,首先是在大环境里,没有学习的氛围。李国彪告诉我们,当时高中毕业之后,不能直接参加考试进入大学,必须先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两年时间,再由相关单位、组织推荐去上大学,那就是现在所说的“工农兵大学生”。
由于推荐上大学的可操作性太强,很多人对上大学都失去了信心。成绩一向良好的李国彪,也曾见到过成绩、表现不如自己的同学,被推荐了上去。
因此,1977年恢复高考的消息一传来,李国彪仿佛看到了希望,立刻与已经担任民办教师4年的哥哥一起报了名,参加了考试。几个月后,录取通知双双到来——李国彪兄弟俩同时考上了大学!这一前所未有的好消息在整个临武县引起了轰动,连《湖南日报》的记者都闻讯赶来,对他们进行了采访。
可是来到湖南农学院的最初那段时间,李国彪的心情并不是很好。本来,去考大学,就是为了跳出“农门”;但农学院那放眼望去整片整片的茶园、农田,总是时时让他感觉到,怎么好像又回到农村去了!
不过,校园里浓厚的学习氛围逐渐影响了李国彪,他开始专心地学习农学专业知识。
“当时的大学生们都十分勤奋,每个人都很珍惜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发自内心地希望在有限的时间里,学到更多的东西。”李国彪告诉记者,当年考上的大学生,年龄悬殊较大,其中80%有过下放经历,所以非常懂得知识和学习的可贵,也不遗余力地汲取知识。“那时候上课、自习完全不用考勤,大家都很自觉,晚上回到寝室之后还自发地看书看到深夜。”
而在大学的学习生活中,最让他觉得受益匪浅的,是随着视野的开阔,他更清晰地认识到了,学习不能松懈,一定要不断地补充新的东西、不断地充实自己。因此,即使是在毕业后进入农业系统工作的日子里,李国彪仍然坚持不懈地学习充电,逐渐成为我市颇具实力的农学专家。
记者手记:
高考给七七级大学生带来的最大改变,莫过于学习意识的觉醒和学习习惯的养成。哪怕是没有考上大学的七七考生,学习意识的觉醒也令他们的人生发生了巨大的转变。在采访时,记者曾接触过嘉禾县宣传系统李小五,他就是当年参加过1977年高考但未能如愿的一名考生。
提起当年的高考对自己带来的影响,李小五同样感触颇深。虽然没能获得上大学的机会,但“知识改变命运”的新观念却根植在了他的头脑中。随后的工作和生活中,他不断学习进修,进行文化补习,如今已通过自己的努力和实力,在文化系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Ⅳ:脚踏实地才是对自己最有利的
受访对象:
李育成,耒阳人,1957年出生,参加高考前为下放知青一员,曾任民办教师;1977年考入湖南医学院,毕业后回郴工作,现为主任医师,任郴州市精神病医院副院长。
1977年上半年,下放到耒阳县盐沙公社前进大队的李育成刚被抽调到大队小学担任民办教师。国庆节回耒阳城的家里休息时,他的姐姐有些激动地告诉他:国家准备恢复大学招生考试制度,当年冬季就会举行考试!
听到这个消息,李育成又喜又急:喜的是国家终于能给他们年轻人这个梦寐以求的好机会了;急的是自己高中毕业已经两年多时间,不少知识都淡忘了,而那时距高考时间又只有短短两个月,自己在大队小学担任班主任,还兼了几个班的其他课程,几乎没有复习时间。
但在“考大学”这一迫切愿望的支撑和促动下,李育成还是尽量进行了一系列复习。回到大队小学后,他把自己以前的中学课本找齐,白天教学,晚上挤时间恶补,每天晚上都复习到深夜,才恋恋不舍地去休息。
高考的前一天,李育成独自走了几十里路,来到了他的考点——夏塘区耒阳七中。考试进行了两天,第一天上午考语文,下午考数学;第二天上午考政治,下午考理化。
李育成回忆,当时的考场管理不是很严,一个考场40来个人,只有一个老师监考,但是考风很好,没有人东张西望或交头接耳。
而让李育成嗟呀不已的是,由于当时深受“四人帮”“读书无用论”的影响,大家平时都没怎么注意学习,结果做起比现在高考题目难度低很多的试卷来,还是一头雾水。在做政治试卷的名词解释时,还有人闹出了笑话——他将“生产关系”解释为“生产队男人和女人的关系”。
这次考试,李育成凭着扎实的知识功底考上了线。就这样,李育成开始了他的大学生活。30年后,当他回忆起当年的大学生活时,最深的印象是,那一届的大学生除了格外发奋好学之外,还有一个显著特征在于都比较稳重宽容,不容易冲动,尤其是年纪较大的学生。
“我们中的大多数都是经历过社会的人,不是下放知青,就是从工厂里考过来的,对人生很多问题都看透了,真正觉得只有脚踏实地才是对自己最有利的。所以后来直到78级、79级的学弟学妹们进校,他们发动的运动或打架之类的事情,我们从来不参加,就是一门心思地想把书读好。”
记者手记:
经历了30年风风雨雨的高考,在怀有不同心态的众多考生和关注者的眼中,越来越呈现出灰色的状态。然而,在考生指责高考制度不合理的时候,在大学生抱怨毕业之后找不到工作的时候,在社会呼吁废除高考的时候,大家有没有想过,作为人才选拔途径的高考,是不是真的已经到了不需要存在的阶段了?而作为知识传递载体的人的本身,又已经缺失了什么?
李育成所指出的77级大学生与当代大学生的差别,或许就很能说明问题。很多人颓废地说,知识已经不能改变命运了。其实,如果没有脚踏实地、奋力拼搏的精神和毅力,恐怕任何东西,都一样是无法改变命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