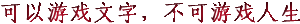[face=楷体_GB2312]
我十五岁下放到沅江的时候,全部的家当只有一口箱子,里面是我自己打点的行李:一床盖被,几件衣服,再就是小刀啦、弹弓啦、陀螺啦等一些自制的玩具。说是知识青年,其实更像一个流浪儿。事实上也只是小学断断续续的读了,中学上了几天课,加上文革中“停棵闹革命”所打的折扣,实际的文化水平大概只有小学三、四年级了。
到了农村,每天除了出工,便无所事事。精力过剩,也没感到什么空虚,只是时间有多,就到处闲逛。在邻近的一个知青点,我结识了一位对我的一生影响很大的姐姐。
她大我四岁,正规的高中毕业生,出生知识分子家庭,也是所谓的“黑五类”子弟。我的懵懂无知很快就引起了她的注意。有一天,她把我叫到她的屋里,要我写封家信给她看。这可难住了我。我虽然上了几年学,但似乎就没有正经写过一篇作文。我写得一头大汗,才憋出个我自己都看不下去的“文章”。她看后没说什么就让我走了。第二天,她找到我,与我谈话,了解了我的家庭和境遇。她长长地叹了一口气,然后看着我的眼睛说:“你做我的弟弟,好么?”对于当时家庭破败,身世飘零的我来说,这句话就像寒冬中的一缕阳光。我想都没想,就说:“好,姐姐。”还向她行了个礼。她笑了笑,从挎包里拿出一本书放在我的手上。“弟弟”她很认真的说:“你不能就这样下去,太可惜了。”我一边听她说话,一边看这本书的封面:在一个硝烟和烈火的背景中,一个瘦削的青年在振臂呼喊,好象又在行进中,他戴着那种我当时觉得很奇怪的尖顶的帽子,后来我才知道那是战斗在苦寒之地的苏联红军战士的军帽。这个青年便是我通过书籍结识的第一个英雄——保尔·柯察金。
就这样,姐姐将我带进了看书的生活。起初,有许多字我都不认识,许多生僻的词我也不懂意思,许多深奥的句子我看不透。姐姐便开始辅导我。给我讲解书中故事的背景,告诉我一些与书中内容相关的东西,告诉我查字典,帮助我把字写好。这位姐姐在我眼里是最称职的老师,她教我的知识都非常乐意接受。她又像个书库,能源源不断地满足我阅读的渴望。我的日子好象重新开始了,一些高尚的人物走进了我的心灵。我浮躁的喜欢讲狠斗勇的个性也变得收敛一些,含蓄一些。我为爱德蒙·邓蒂斯的蒙冤下狱而愤慨、不平;更为基督山伯爵复仇的周密和到位扼腕叫绝。我对斯巴达克斯替他的战友克利可刹斯举行的葬礼佩服得五体投地;也被他对范莱丽雅火热而执着的爱情深深感动。我佩服牛虻的坚毅,我欣赏少剑波的才情,惋惜书中那些义薄云天的英雄走向末路,也遗憾于那些断肠心碎的儿女情长。特别是书中的爱国的,民族的那种七壮山河的气概常常让我热血沸腾,我总不自觉地把自己融进书里去,这样一来,现实的苦楚和不快有时便离我远了许多。
书成了我离不开的精神食粮,我的所有空闲的时间都用在了这上面,。甚至夜间,我都打着手电筒在蚊帐里看书。我一生中所读的文学书籍,大部分都在这个时期。
姐姐并没有放手让我随性去读书,而是不断的指导我。对每本书她都作了阅读要求,不许我囫囵吞枣地读,至今我读书都非常仔细,这都得益于她的教诲。每读完一本书,她都要我谈心得,我的口头表达能力在这一时期提高不少。后来她让我再写一封家书回去,果然得到了父亲的赞许。
后来我虽然没有成为文人,但这段读书的日子让我获益匪浅,也终生难忘。
这位姐姐是我一生最值得称之为良师益友的人,她的名字叫做:杨碧霞。她现在已经离开了这个世界,愿她看到我写下的这些不能称为文章的文字。[/fa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