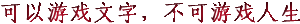难忘的友情
记得那是我们刚到靖县甘棠不久,队里安排了一部分劳力烧石灰,我们四个男知青自然也去了。
烧石灰无非是这么几道工序:打炮眼和装填炸药,点炮,碎石,上窑(挑石灰石),烧窑(装加柴火)等,我们开始去时主要是挑石灰石,过了一段时间又开始打炮眼,填炸药,这倒是有一点技术要求。主要是选炮眼的位置,打炮眼的角度和深度,再就是填炸药时放引信有点技术。不过这些都难不住我们,在学校我们打井时,曾搞过爆破,还请了工程兵学院的教官来上过课。所以这些事我们很快上手了,而且效率比队上的其他的人还高点。
后来我们也参加了点炮。这是个很刺激但又很危险的活。尤其是排除哑炮危险最大。我因为在学校打井时经常下到几十米深的井中排除哑炮,现在在地面排除哑炮又有何难?所以每次出了哑炮,我都积极争取去排除。
有一天,终于出事了。那天点完炮,一阵爆炸声后,发现有两个哑炮。我按规定等了几分钟,炮还没响,应该是可以去排除哑炮了。第一个哑炮的引信和雷管很顺利的拉出来了,成功排除。第二个哑炮的引信我拉了几下觉得很松,但埋得很深,于是我侧过身子去拉,不料这时突然爆炸了,我的右手手掌炸开了一条缝,右胸炸了一个小口子。幸亏这个炮眼没塞紧,只炸起了一些碎石子。
回家后,队上的知青同伴赶快帮我清理伤口,先是把嵌在胸口和手掌表面的碎石清理掉,又用碘酒消了毒。这时伤口已经不流血了,好像也不太痛,大家细心的帮我包扎好,就让我去休息了。
第二天早上我一醒来,头有点重,手好像也肿了,胸口的伤口也开始有点发炎的感觉。但我并没有在意,感觉这不过是皮外伤,过几天自然就会好的。
起床的时候,发现问题有点严重,右手好像有点不听指挥,全身也软绵绵的没有力气。我奋力挣扎着站在了地上,闭了一下眼睛,平息着突突的心跳和那种心悸的感觉,准备去拿手巾洗漱。这时我们的知青管家从楼下端着一盆洗脸水进来了。“别动!你的伤口不能沾水”,看见我准备去拿脸盆中的手巾,管家连忙喊道。我疑惑地看着她,她很快地把手巾拧干,说:“我来帮你!”“不用不用,我自己来。”我的脸一下子红了,用左手接过毛巾,胡乱洗了把脸。说实话,我这人一向不习惯受别人照顾,更别说受女同学的照顾了。当天,我无法出工,只能在家休息。
第三天,伤口开始恶化,已经化脓了,并且体温也开始上升,看样子是发烧了。大家决定,由管家送我到公社卫生院去就诊。
在卫生院,医生帮我抽出脓血,并清除了手掌伤口里面的碎石(就是这些碎石让我受罪),在伤口里塞进了很大一卷药水泡过纱布,然后把手包扎起来,用一根纱布把手吊在胸前,真像个伤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