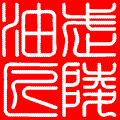(十)
于兆确实也很想把队里的生产搞好,为了提高劳动效益,今年他将薅稻实行按面积包干计酬办法。于明的父母都是队里有名的精明人,听说今年薅稻采用五人一组自由结合,按面积计酬的办法后,就邀了于兆的老婆和他们家的四个劳力合为一组,并要求负责承包队里所有的大块水田。于万章明白其中蹊跷,但并不示弱,他家也有四个劳动力,就邀了王全尚的老婆桂枝参加他的这一组,声称也要承包队里所有的大水田。于兆与王全尚两个队长只好坐下来商量,将队里的大田分为二份,二个组各承包一份。其余的几个组承包的都是那些小块的水田。几天下来,各个组在田里耕作的时间相差无几,可是承包大水田的二个小组所获得的工分比其他组的工分要高得多,而且还高得蛮离谱。于峰、于明、朱云龙、犟脑壳心里明白是怎么回事。于木匠是个无利不起早的主,本想揭穿这套把戏闹起来,可想想自己时常“犯规”,都是于兆和王全尚在关键时刻放了他一马,也只好选择了沉默。后来才知道承包大田的几户人家只在大田四周薅一圈,当路的地方再补薅几行,等队里验收的人来了,就在大田中间走几圈搅浑水,应付检查。大田中央根本没有薅动过,负责验收检查的人怕得罪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这些稻秧根本没有分蘖,草长得比禾苗还要高,都没有结谷,亩产不足百斤,真是人哄了地皮,地皮哄人的肚皮了!这种骗人骗己的把戏的结果是,年终决算上坪生产队又是全大队最次的一个。再多的工分,只是一个文字符号,得不到任何实质性的东西。还有一个问题的结症:分配办法不公正,严重影响了社员的积极性。上坪生产队人少田多,要鼓励劳动力多的农户踏实耕作,提高全队社员的积极性,就应采用按劳分配,多劳多得。可队里的做法却反其道而行之,每年制定分配方案时,他都要将人口分配的比例加大,实行倒三七、倒四六的方法。这是因为队干部们私心太重。例如于兆的家里劳少人多,他两口子劳动养着五个小孩,这样分配,连抱在怀里吃奶的孩子也跟劳动力一样都能分到一份同样的口粮。这样就造成了劳力少的农户岁岁有余粮,多劳户年年缺粮的不合理现象。于兆没有文化,鼠目寸光,只看到了眼前的蝇头小利。他不会算这本帐:其实粮食增产了,人均口粮同样会增加,他的家庭分到的粮食也会更多。
小英被金牛滩粮站的一个小伙子看中娶走了,上坪生产队的知青少了一个真心关照他们的热心的伙伴。
小英姓丁,全家有五口人,母亲是位非常能干的女人,父亲由于身体不好,不能从事重体力劳动,他与钱师傅、于瑞每人负责看管队里的一头牛。家里还有一个妹妹和一个弟弟,年纪还小都在读书。全大队丁姓人家都基本上集中在英湖边,小英家的住房也在丁姓屋场边上,她的家距上坪生产队相对远了点,是上坪生产队唯一与于家没有任何瓜葛的人家。傍着桑荫学种瓜,小英从小生活在农村,儿时做游戏都学着大人的模样,就这样一点一滴地积累了丰富的农村生活知识。知青下放到上坪生产队后,小英的年纪与小牛、小伍相仿,每天一起出工,又一块儿收工,浙渐地小英与知青之间建立起了深厚的情谊。知青有了位朝夕相处的伙伴与老师,小英也有了几个好朋友。
队里的贫协小组长于峰是个不错的小伙子,人也长得帅,在队里算是个有能力的青年人。于峰的心中早就有了小英,很想娶她做媳妇。于峰的母亲还请人去说过媒,丁家没有答应,主要是队里太穷,小英也不愿留在这儿再受一辈子苦。上坪生产队像于峰这样的帅小伙,还有好几个都没有说上媳妇。不久前,金牛滩粮管所有个吃国家粮的工作人员看上了小英,说实在话,这小伙子的模样要比于峰差多了,但小英答应了这门亲事。小英悄悄告诉小牛,这小伙子家庭条件不错,每月还有二十多元工资,她嫁过去后再也不愁吃、不愁穿了!尽管当时她还没有到达法定结婚年龄,但她父母想办法请人将户口的年纪改大了,才去办了结婚证。
姑娘如果嫁了个好人家,回娘家是很风光的:女婿挑着箩筐走在前边,一头放着孝敬岳父岳母的礼品,用大红纸盖着,另一头坐着小外孙。女人跟在夫婿后面,身著大红花衣、绿色花裤,不管天晴下雨都会穿上“统统靴” (长筒套鞋),在大堤上一路走来,简直就是道亮丽的风景,惹来无数羡慕的眼光。进村后见到父老乡亲就一个劲地大声招呼问候,唯恐别人不知道她回来了。外公外婆见到女儿、女婿、小外孙,接过丰厚的礼品,脸上乐开了花,自然是将之奉为上宾招待。小英第一次回娘家就再现了以上一幕:她剪了个很时髦的短发,穿着当时最高档的毛哔叽裤和灰色的确卡衣服,尽管是晴天,她还是穿着那双女孩子们梦寐以求的“统统靴” 。要不是她主动跟人打招呼,大家认不出她了,都说:“小英到了‘好疤迹’,像个‘街吧佬’(城里人)”。
小英嫁到的金牛滩距太平港公社有三、四十里地,每年只有过年过节才回娘家几次,虽然她与知青见面的机会很少了,可知青们都由衷地为她高兴,也祝愿这位好心的姑娘从此过上幸福美满的生活!
民兵排长于万朋与于万权是亲兄弟,可差异很大,不仅长得眉清目秀,还是个热心肠的人,经常帮助队里的知青。大牛他们自己开伙后,他拿来了一只老母鸡和十几枚种鸡蛋,二十来天后,孵出了一窝小鸡。小牛、伍晓别提有多高兴了,天天精心饲养,两三个月后,小公鸡早上就会打鸣催人起床了,小母鸡也开始“咯咯”叫着下蛋了。知青屋里热闹了起来。最可喜的是经常可以吃到炒鸡蛋和鸡蛋汤,这自给自足的晕菜,吃起来格外香甜!
小牛是个“霸蛮”的女孩,每次在杨李垸、吴家荡出工休息时,见队里的男子汉去开潭挖藕,她闲不住也跟着去,回来时一身稀泥巴,连头发根上都湿漉漉的,只见她腋下夹着铁锹,左手提着粘满泥巴的胶鞋,右手指头勾着用松垮垮的草绳捆着的几根糊藕,一边笑咪咪的走过来一边大声说“哥哥,今晚有藕片吃了!”大牛见妹妹真的还挖回了湖藕,脸上也在笑,可见她搞成个泥猴子样,心里又着实心疼。
知青种点儿菜确实不易,眼看着菜园子里种的一茬菜马上可以摘来吃。却不料头天除草浇水后未关好扎紧菜园篱笆门,次日被一群鸡钻了空子,把满园的菜糟蹋得不成样子,准备采摘的那畦菜已被啄成了“光杆司令”。播的菜种才刚刚萌芽,也被翻了出来,柔嫩的根芽都被太阳晒蔫了,看来这一茬菜的“小命”很难缓过气来。小牛和小伍见此情景,一边整理着菜地,一边抹着眼泪。此情此景,借用一首唐诗里的句子:“但见泪痕湿,不知心恨谁”来形容,虽说有点牵强,倒也还形象。有时还发现菜园子里明明有不少菜,可是第二天去摘时却莫名其妙的不见了,岂不怪哉!
有次,小牛内急回来方便,顺便到屋取东西,远远看去怎么菜园柴门未关?她清楚地记得自己清早出菜园后是关了门的,怎么又打开了?这就纳闷了。她赶紧走近一看,原来是钱师傅在摘自己的菜。小牛终于找到了最近经常丢菜的答案:原来自己辛辛苦苦种出来的小菜,是这位老人家“帮忙摘去了” ,小牛好言劝他不要再来摘菜了,可是钱师傅根本不听,还凶巴巴的挥舞着拳头想要打人。小牛也不怕,要他马上滚出菜园,老羞成怒的钱师付用拳头朝小牛挥了过去,小牛与他扭打起来,可一个女孩子哪是他的对手?结果钱师付揍了小牛一顿,拿起摘下的菜扬长而去。
钱师傅其实也姓于,年届五十却孑然一身,与见章、章瓦匠属么房中的一支,该是爷爷辈的人物了。但因为其貌不扬,又经常干傻事,晚辈们当面叫他“钱师傅”,背地里却叫他“钱戆棒”(不聪明或弱智)。早些年钱师傅不慎失火烧了住房,原本贫困的家更是一贫如洗了,只得寄居在见章家的堂屋里。土砖搭着几块木板,垫上厚厚的稻草就是床。床上的蚊帐与棉被是火灾后民政部门救济的。泥巴糊着几块砖支着口铁锅,是个标准的圆型灶。一双筷子,两个碗,一口水缸,一个笠箕,这就是钱师傅的全部家当了。
因为人不聪明,又无劳力,几十年来,钱师傅只能给生产队看牛。每日晨曦初上,钱师傅就与老黄,于兆二老一小牵着队里的耕牛走出牛棚,大声吆喝着:“尿尿!尿尿!” 耕牛尿尿后,便沿着田梗或渠道去吃青草,钱师傅也开始了一天的工作。
钱师傅母亲在弥留之际,久久都不眠目,想说点什么,可一句话也没法讲出来,两眼直盯着自己的儿子。邻里们见状都十分清楚,老太太一生的祈盼,是能为儿子娶上媳妇,再生下一男半女接上自家一缕香火。只怪当家的人命短去世得早,留下母子二人艰难度日。这些年队里生产不景气,能吃饱饭就不错了,那儿来的余钱剩米挪作他用,加之儿子心中也不亮堂(智商不高),又没有遇到与之相配的女人,自己已尽了最大的努力还是毫无办法,就这样一年又一年将娶媳妇的事给拖了下来,儿子的年纪也越来越大……。
母亲死后,钱师傅渐渐地死了娶媳妇的心思,过着一个人吃饱全家不饿的单身汉生活。有人经常跟他开玩笑,说要给他娶个媳妇,特别是队里几个能说会道的泼皮,闲得无聊就拿他开涮,钱师傅每次都特别认真地听,有时也居然听得春心荡漾起来,哈哈地傻笑,又像是得到了某种满足,哈喇子也情不自禁地流了出来。
钱师傅日日为了温饱而忙碌,然而现实生活依然事事都不如他的愿,就开始麻木了起来,菜园长满了杂草也懒得去锄,荒芜了。在看牛时,今天在东家摘一个瓜,明天在西家掐几根菜,反正每天在看牛回来时手不空,多多少少总有点收获,够一人吃就行了。如果有人瞧见了,只要不是自家的东西,都会视而不见保持沉默。也有人发现是自家的菜后就破口大骂,钱师傅也欺软怕硬,碰上凶很点的人家,下次就不敢造次了。这样防他的人越来越多,可猎获的地方越来越窄了。
知青种的菜都长出来了之后,他便又有新的地方光顾了。知青出工与钱师傅看牛的时间是错开的,正常情况下碰不到面,而能看见他进知青菜园摘菜的人,都不敢劝其半句。久而久之,做这样的缺德事成了他的习惯,他进知青菜园摘菜仿佛跟进自家的菜园子一样从容不迫。不想这次被小牛发现了。事后于瑞等人撺掇大牛好好教训他一下,可大牛见到他那猥琐的模样,又不忍心下手了。
其实,钱师傅也是个可怜人。一辈子没有吃过几顿象样的饭菜,没有穿过一件体面的衣服,也没有被他人尊重过,除了得到过母爱,再没有一个女人用正眼瞟过他一眼。与其相伴的只有贫困和孤独。这样的人,你责 怪他、教训他又有什么意义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