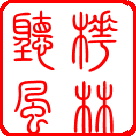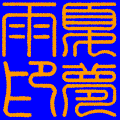渔痴
(作者:浏阳知青磊石先生)
我在仙洲当知青的第一个住户户主,是位老实巴交的农民,我们叫他水叔。
他没上过学,斗大的字认不得几个。然而队里扶犁打耙的等卖力气又要功底的活,他样样拿得起。兴许是与“水”沾缘,他最讲究最有瘾的是打渔。
那时他己进天命之年,可身子硬板得有如后生。只要一去打渔,便快活得像小孩似的。
不顾一天的农活劳累,只要天气好,他三口两口扒完晚饭,就卷好“嗽叭纸烟”吸着,背上鱼网,挎着渔篓,一双赤脚,哼着不知名的调儿,悠悠地往洲上去了。
当我迷迷糊糊要做梦的时候,水叔回来了。厅屋灶下里一阵响动,我似睡非睡地闻到了只有河溪才有的新鲜水草味鱼腥味。接着又能听到“巴嗒巴嗒”抽草烟的声音。
第二天早上靠得住有鲜美的鱼吃。
春夏时节,常常落大雨.一待落得河水上了浅岸,上了沙洲,他眼睛就放亮,格外的来精神。
他在咧咧的微笑,我帮他递过斗笠蓑衣,他麻利地穿戴整齐,从大门角落搬出长长的鱛,又从碗柜里取下一只酒瓶往背篓一塞,便碎步朝大河边跑去。
有时我跟了去帮他提渔篓。他总是比别人要早几步抢占了回不湾的有利“据点”轻松地把丈把长的鱛网往浊水里一沉,稳稳地守在河边梗树下。我就在他身边蹲着,盯着鱛杆的动静。他守候起鱛的时候很有节奏,当然是慢板。而正是这种缓慢起沉,与大河涨潮的急流成了鲜明对照,很有韵味。每一次起鱛,我免不了紧张,盼望网到大鱼,总担心网鱛里是空的。唯有水叔,不急不恼,心平气和。拉上来不少鱼虾,他不忘乎所以;扯起来只有水草漂屑,他也不摇头皱眉。我于是注意观察起水叔来。一起鱛,他便生龙活虎,充满阳刚之气。一沉下网,他就蹲着,低头抽着烟或呷着酒,斗笠压得看不见脸,人像石雕一样动也不动,与河与溪与树与雨构成一幅淡墨山水画。水叔不懂得诗情诗意诗境,却正是他本身与自然创造了诗情画意。
队上有人告诉过我,水叔有一次下半夜在溪畔打鱼,困了就一丝不挂躺在草地上睡着了。一个放水的社员路过,见岸上有一只盛着鱼虾的渔篓,很是惊讶。水叔刚好醒了,以为有人想偷他的鱼,便从后面一把抱住那人,吓得老走夜路的放水人扔下渔篓,没命地跑了。水叔才从树丫上取下晾着的衣裤穿上。天冒亮,他提着打来的鱼过河到镇上卖,照例买些肉、酒、盐什么的回来。
水叔为了生计打鱼,也是为了生活打鱼。打鱼也解决了一些生计,但更多的是回报了他生活的乐趣。而我到了他家后,打鱼与生计就分开了。
他的一个同样爱打鱼的儿子对我说:你们没来时,我爹打的鱼都卖了;你们来了后,打的鱼都上了吃饭桌。
从此,我心里总装着那幅打鱼的“画”和画中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