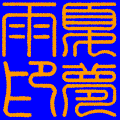[ 枫林过客,江永老知青,后转点到浏阳。著名知青网络作家;曾在《榕树下》、《红袖添香》等文学网站发表文著数十万字。 ]
(一)
莺飞草长,柳绿桃红,正是山里四月天。位于允山区深山里瓦扎湾村的红星小学——确切地说,是整个瓦扎湾村,都乱套了。大人孩子,男男女女,从全村各个角落汇拢来,小学操场上挤满了人,沸沸扬扬、喧闹不已。
长沙知哥,大家都熟知的宪哥,山村小学代课老师谭宪的尸体已从老山冲里深水潭里打捞上来,现在正直挺挺地停放在小学办公室的门口。
是失足落水还是投河自尽?大家议论纷纷,莫衷一是。
(二)
青山环抱,清流小涧,座落此处的红星小学只有两个混合班。两个老师,一男一女,都是二十多岁的年轻人。男的就是长沙知青谭宪,教语文;另一个教数学的则是女老师余芳,是原瓦扎弯大队支部书记余国雄的女儿。村里成立革委会后,老余已靠边做了个大队的办事员,只在村里做些上传下达的活儿。
瓦扎湾村傍依都庞岑山系小古源冲。四面环山,仅余一条六尺宽的简易泥路,据说原本为咸丰年间的古驿道的旧路底子。原来此路满铺青石板,逶迤直达山口,只是经年毁损,且被当地山民挪作他用,于是,变成了今天一条光光的泥巴路。此路绵延十数里,一直通到允山闹子上。红星小学临涧而建:三间屋子,两间是教室,另一间呢,前半间是学校办公室,后半间则是即宪哥的住房。
小学无围墙,显得操场非常开阔,常常是村里晾晒农作物、开批斗大会的地方。
宪哥从长沙插队落户到瓦扎湾的那一天,是1964年9月13日,应是长沙知青三批下放江永的第一批。宪哥外貌看去白净瘦弱,手无搏鸡之力,且平时出工捞分也不积极,有“懒人”之称。但此人出身书香门弟,自小浸淫文学诗词,有极好的文学底蕴和口才。寂寞山村里无任何娱乐所在,当地山民也就是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瞄了那落山的太阳,吃过了,洗了脚,有老婆的汉子即搂了那团柔美的肉身去享受他唯一的快乐;没老婆的汉子就卷起一根“喇叭筒”吸着,呆呆地猫在门楼上打发时间。自从宪哥一干长沙知青来到这个瓦扎湾后,山村里顿时热闹起来。当地山民也不会那样早就去睡觉了。他们三五成群,男男女女经常到知青组看城里来的伢妹吹笛拉琴,看唱歌跳舞。瓦扎湾山村的黑夜变得短了。
宪哥既唱不得歌又跳不成舞,但他却成了当地山民乃至男女知青最愿意靠拢的角色。他很少洗澡,身上有“异味”,但大家愿意紧靠他坐下;他不出工,没有粮食菜蔬,但大家愿意供他吃喝。怪事!
原来,宪哥有一绝会讲故事。他讲的《十二金钱镖》,讲的《七侠五义》,讲的《陈查礼探案》如同一丛饱含蜜汁的花卉吸引了众多的蜜蜂。他们个个讲:听宪哥讲故事,那确实是种享受,宁愿三天三晚不睡觉!但宪哥不会让他们不睡觉的,每到当紧之处,他便会以一套白口路子:要知…,且听下回分解。这是宪哥为自己的“生计”留的后手。于是,大家只得依依不舍地起身,寻思着明天备好吃喝来继续这种精神“享受”。
宪哥的这种有吃有喝的“好日子”持续了二年,却因为文化革命这场运动的到来而中止了。那时候,江永的武斗愈演愈烈,还成立了什么“贫下中农最高法院”。而这个“最高法院”是最恨长沙仔的,恨不得把这些长沙仔长沙婆都判了死刑。那年八月,下放在江永的长沙知青跑了个十室九空。命都是人家的,谁还愿意听故事?因此,宪哥讲故事的“生意”顿时清淡冷落下来。没了“生意”,宪哥那段日子过得十分凄惨潦倒。
宪哥看来是回不了长沙了。他没有一分钱盘缠,路上寸步难行;他己是孑然一身,回长沙根本无处落脚。说来可怜,他在长沙的那唯一亲人,做小学教师的母亲也被当作漏网的地主分子揪出来,连斗带病悲惨地去了另一个世界。
好在宪哥在瓦扎湾乃至整个允山是个“名人”,不管是当地山民还是当时贵为“贫下中农最高法院”的造反者们,都知道他是个能给大家带来快乐的故事大王,神得很!他虽是依然那样吃了这餐没下餐,衣衫褴褛,神情落拓,但没有人来捆他,也没有人来指认他是地主狗崽子。间或还郑重其事地备有酒莱来请他去讲故事。
宪哥似乎与其他知青彻底“划清了界线”,神奇而安然地度过了这段其他知青谈虎色变的凶险日子。
“石头也有翻身之日”这句市井俗语居然验证在宪哥身上。
有人讲他走“狗屎”运,走不走运无法验证,但让他当上了有十几块钱奉禄的山村小说代课老师倒是一点也不假。
那是1971年9月13日。说这个日子不同寻常,一是中国政坛的二号人物、“副统帅”林彪叛国出境,在蒙古温都尔汗机毁人亡。不过,中国发生的这一重大的政治事件,普通老百姓们过了好长一段时间之后才听到了上级传达的文件。如此一来,知青的生存状况有了一点转机;其次是宪哥9月13日这一天正好下乡七年整。让瓦扎湾人大吃一惊的是,平时有“懒人”之称仅凭一张嘴巴东游西荡的谭宪同志,竟然被允山公社革委会的欧主任看中,让他参加培养革命后一代的革命教育工作:由他接手一位年届六十的老教书先生的教学工作,担任瓦扎湾红星小学的语文老师。
其实,余国雄一开始也不愿意接受这个谭宪。平时看他吊儿郎当,混吃混喝,实在不堪为人师表。讲得严重点,莫要让他玷污了神圣的教育事业。但是,在公社革委会,欧主任拍拍老余的肩膀,满脸笑容却不容置疑地说:“老余,你是老前辈了,顾全一下大局吧,要相信人总是会改变的。共产党连国民党战犯都要改造好,还在乎一个谭宪?”
欧主任听过宪哥讲的故事,他觉得宪哥是个人材,教小学是绰绰有余。
老余再也推辞不得,只好答应下来。
说起这个宪哥,让人感觉心酸。
宪哥自小肝脏不好。初中毕业以后,与他同龄的年轻人都满怀豪情地奔赴农场或插队落户去了。他的母亲则考虑到儿子体弱多病,于是,为他四处奔波,想方设法让他进街道工厂工作。突然有一天,街道来人通知谭宪去湖区插队。做母亲的急了,拉了儿子匆匆赶到街道,竟不顾为师之尊,“扑通”一声跪下了,苦苦哀求道:“他是一个有病的人,到了湖区怎能适应那里挑堤的劳动强度呀?……”街道头头跷着二郎腿,冷着脸说:“根红苗正的工人子弟都要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何况你们这些出身不好的,不更要改造思想?”看着母亲长跪不起的凄凉景象,宪哥心如刀绞,他用力去拉母亲,哭着说:“去就去,大不了一死。”到了最后,那街道头头似乎动了恻隐之心:“这样吧,上山下乡是一定要去的,名额已下来了。考虑到你们的特殊情况,就照顾到有山有水的江永去吧。”谭宪的母亲忽然想起在郊县乡下有一门早已不相往来的远房亲戚,那儿与长沙相距不远,来往方便,而且又是比较富庶之地,但街道上就是不同意,提出谭宪的名额只能上山下湖,否则连“换地方”的优惠也没有。无奈之下,宪哥插队落户到了江永山乡。
自从下乡以后,原本活泼好动的宪哥似乎变了另一个人,整天沉默寡言,神情忧郁。尤其是从大都市插队落户到这江永的偏僻山村,更使他感到命运多舛、前途渺茫。看到本大队一些知哥学木匠,跟着去试了半个月,终究不是料。于是,他干脆来个做天和尚撞天钟,开始了混混生涯。
这次真是母亲在天保佑,天上掉下个有月薪的差使。
宪哥刚来到瓦扎湾时,山村里的小学只有一个班,原来的老师就是那位终生以私塾为业的老教书先生。这位老先生年轻时也未上过正式学堂,读过几年之夫者也的私塾,对新的教学内容接触甚少,但为人古板认真。山村闭塞,少有文化人进来接手教书。于是,村里倒也接纳了这位老先生。
及至村里人口渐多,小学又扩了一个班,新来的老师就是原大队支书余国雄的女儿余芳。
(三)
常言:性格决定命运,而历史铸就性格。生活的无奈往往注解着这句话的后半部分。人,既有劣根性的一面又有闪现善良人性的一面。宪哥在成为革命教师队伍的一员以后,外表一改肮脏落拓的形象,代之以整洁儒雅示人;慵懒混世己成为过去,勤勉认真兀现教师育人新风。宪哥变了,变得让人觉得可爱也是可亲近的了。
孩子们最喜欢的是在课余围着谭老师,听他讲述着长沙的大马路、高洋楼、清沏的湘江、人山人海、五光十色的商店。在这种时候,我们的谭老师往往不是使用上课时的江永官话,而是操着一口呦口的长沙普通话,让孩子们倍感新鲜和亲切。有时余芳老师也在一旁听着,听到有趣之处,便掩嘴一笑。那时候,孩子们语言频率最高的一句话就是模仿谭老师的口头禅:“要得噻!”
长沙,在全国大城市并排不上号,却是这些从没有见过世面的山里孩子最向往的省会大城市。也许在这些少年的梦想中,长沙是一个挥之不去、永远牵挂在心中的情结。
“谭老师,长沙的烈士纪念塔真的很高很高、仰起脖子一看帽子都会掉下来吗?”
“谭老师,长沙的五一路好宽好宽的吧?”
“谭老师,长沙的公园好漂亮的吧?”
……
孩子们甚至在梦中都向谭老师七嘴八舌地提问着各式各样稀奇古怪的问题,而梦中的谭老师总是和蔼可亲地一一作答。
谭老师还许诺,等你们长大了,他就带着大家一起去长沙玩玩。
宪哥其实还有一种长处:他会修收音机。下乡时,他从长沙带来了有一只旧的半导体收音机,因为有毛病,一直丢在箱子里,经他几个晚上的修理,终于会唱歌了。这东西在乡下可是个稀罕物儿。记得那年到允山开社员大会第一次听了广播喇叭时,几乎全村的男女老少全都惊奇地瞪着主席台旁那个大喇叭。或蹲或立、屏声静气地听着广播喇叭里的各档节目。大家都觉得奇妙极了,一根电线通着一只喇叭,就可以听戏、听歌、听人说话、听“最高指示”。但是,谭老师的那只半导体收音机更加令人着迷了,一天到晚都有节目,而且能收听到十几个电台。每天放学后,总有好多同学不愿回家,到学校办公室聚在一起听收音机。不知不觉天已黄昏,直到谭老师下了“逐客令”,才恋恋不舍地回家吃饭,还对父母撒谎说是老师让留下来做功课。
每逢星期天,山里的孩子主要的活儿是砍柴禾。总有三五成群的伙伴儿背着扦担柴刀,不约而同地来到了学校。谭老师见了,便笑着问:“又要听收音机了?”随即,他拿出半导体收音机交给他们,让他们自己调台听节目。大家最爱听的是电影录音剪辑。有一次不知谁调到了一台戏曲节目,清丽婉转,十分动听。一个同学说:“不听不听,快收电影。”一旁的谭老师赶紧说:“别急,先听一会儿。”于是,大家就安静地听着。过了一段时间,有人抬头看谭老师,只见他痴痴地听着,眼角竟然还有泪水慢慢地流淌下来。他们不禁叫了一声“谭老师…”他立刻回醒过来,拭去泪水,不好意思地说:“这是长沙的花鼓戏《沙家滨》,妈妈年轻时就是花鼓戏迷,小时候听惯了妈妈唱的花鼓。现在一听,就想家了。”
后来,不知是谁向公社革委会告发,说宪哥晚上偷听敌台。这在“文革”年代,确实就是一个吓人的“现行反革命”案件!台湾特务、里通外国……上纲上线,谭老师够得上坐牢杀头的。结果,谭老师被喊到公社革委会办了几天学习班,半导体收音机也被收缴上去了。好歹查无实据,余国雄将宪哥从公社保了回来。此后相当长的一段日子里,宪哥显得非常消沉,闷闷不乐。村里的孩子们也为谭老师喊冤叫屈,更为他失去了半导体收音机而惋惜不已。
还有一件事儿不能不说。那一年“六一儿童节”,学校组织全体学生去县城游览。班上有个拄着拐杖的残疾学生,因为外出行动不便,老师就把他放假在家。可是第二天清晨,当同学们在学校门口兴高采烈地排队下船的时候,那个残疾学生也来了,落寞地站在一旁,神情孤单而又忧伤。谭老师看见了这个情景,就走过去,俯下身子温和地问道:“你也想去?”那残疾学生轻轻地点了点头。谭老师考虑了一下,转过身子蹲了下来:“那好,我来背你上路吧。”谭老师背着那残疾学生走在出山的那条路时,余老师对他说:“带上他,会影响活动的。”谭老师说:“你带好其他学生,我照顾他。”孩子们一路欢叫着出了山口。谭老师背着那残疾学生上上下下,走山路、到允山、游县城。累得他气喘吁吁,汗如雨下。把那残疾学生感动得不知抹了多少次泪。谭老师也是瘦弱之身哪!所以,当后来,谭老师的遗体从冲里打捞上来时,哭得最伤心的就是那个残疾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