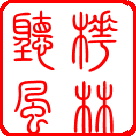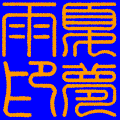踏入了同一条河流(上) .枫林过客 .
题记:哲学家说:人不能二次踏入同一条河流。然而,我做到了,在那时间静止的年代。
一、寻找那条河流
很多时候,人会将自己的人生比喻成在河流中的漂泊。那时候,你被裹挟在激流中,随波而下,顾不得身体的痛楚、顾不得思考你将会流向哪里,你的求生本能会下意识地指挥你自救,为的仅仅是挣扎上岸。
那年,一个风雨大作的日子里,我倦缩在浏阳汽车站的一个角落,忧郁地望着窗外那肆虐的雨点和站外那被雨点溅起水花的肮脏地面,心绪沉郁而莫名。不知什么原故,我这十六岁便早早离家去了湘南农村漂泊的人,突然对浏阳这个离家很近却很陌生的地方感到了一丝恐惧。这个我自小就很熟悉的地名,也只是听听而己却从未去过,我不知道随着命运之舟在生活激流中的颠簸,将被带到哪个孤岛上。
在我的眼前,我的孤岛—浏阳,正踩在自己的脚下。非常熟悉的湘南山峦己经渐次模糊在脑海中了,只留下母亲临行一句告戒的话:“好不容易将你转点到了浏阳,你要好好干……”母者精神一直是支撑儿子有信心在人世活下去的信念,我无法不感念母亲痛惜儿子的那种苦心。二年前发生在湘南的“道县大屠杀”让身在长沙过着“被管制”日子的母亲有了揪心之忧,她千拜托万拜托一位叫幼成的女知青找到了这个可以不问政治出身的“转点”所在,让当时生着病的姐姐揣着盖了十数个图章的“转点证明”只身进入莽莽的大围山林,她是去为我办理户口迁移手续的。所幸,有着熟门熟路的幼成的帮助,仅仅用了二天时间便为我办妥了“人生转折”的一应手续。在那样的年间,一纸户口可以定人生死,这许是当代人难以想象的事。接到母亲的信后,久被大山里沉重的气氛桎梏的我,竟然会有杜少陵当年闻官军收河南河北的那种“初闻涕泪满衣衫”的喜极之情,居然兀自躲在一隅垂泪。在那边知青伙伴们艳羡的眼光下,我稍稍收拾好自己一点不多的衣物,便匆匆赶回了长沙。次日,便在母亲殷殷的叮咛中,乘上了东去浏阳大围山的汽车。
扛着从湘南农村带来的那套家什,我在盘旋曲析的山路上向上攀爬。路旁的松柏和不知名的植物在早春二月的寒风中漱漱作响,犹自穿着的棉衣下面的内衣却早己了无一根干纱了。虽居住湘南大山几年,住地却是大山脚下的平原地带,此次转点的兴隆生产队深隐在大围山中,唐人的“白云深处有人家”一类的诗句便在脑海中盘旋,内心不禁升腾起一种新奇的感觉,尽管以自己当时的狼狈祥子不免有“叫化子”吟诗的酸相。
好不容易将那段盘山路爬完,转过一片竹丛,便听到了鸡鸣狗吠之声。我知道目的地不远了。突地,我的耳畔响起人声:“是到兴隆去的吗?”侧脸一看,一个三十多的汉子扛着把锄头站在坳上。此人五短身材却显精壮,白皙的脸看去不像农人。他笑吟吟地做着手势,将我引向左边一条路,并且将我的行李抢过来扛在肩上,他叫出了我的名字。看得出,他对我的到来早有所闻。
他叫邱清云,是兴隆生产队负责政治宣传的副队长。在一个异常陌生的地方,遇到的第一个对你表示亲和的人,无论是谁,都会心生感激的。我跟随着他,走向了这次旅行的目的地:知青点。我其实是个羞涩的孩子,真要面对一个陌生的环境,我的心不免会突突地蹦跳。
那年,一个风雨大作的日子里,我倦缩在浏阳汽车站的一个角落,忧郁地望着窗外那肆虐的雨点和站外那被雨点溅起水花的肮脏地面,心绪沉郁而莫名。不知什么原故,我这十六岁便早早离家去了湘南农村漂泊的人,突然对浏阳这个离家很近却很陌生的地方感到了一丝恐惧。这个我自小就很熟悉的地名,也只是听听而己却从未去过,我不知道随着命运之舟在生活激流中的颠簸,将被带到哪个孤岛上。
在我的眼前,我的孤岛—浏阳,正踩在自己的脚下。非常熟悉的湘南山峦己经渐次模糊在脑海中了,只留下母亲临行一句告戒的话:“好不容易将你转点到了浏阳,你要好好干……”母者精神一直是支撑儿子有信心在人世活下去的信念,我无法不感念母亲痛惜儿子的那种苦心。二年前发生在湘南的“道县大屠杀”让身在长沙过着“被管制”日子的母亲有了揪心之忧,她千拜托万拜托一位叫幼成的女知青找到了这个可以不问政治出身的“转点”所在,让当时生着病的姐姐揣着盖了十数个图章的“转点证明”只身进入莽莽的大围山林,她是去为我办理户口迁移手续的。所幸,有着熟门熟路的幼成的帮助,仅仅用了二天时间便为我办妥了“人生转折”的一应手续。在那样的年间,一纸户口可以定人生死,这许是当代人难以想象的事。接到母亲的信后,久被大山里沉重的气氛桎梏的我,竟然会有杜少陵当年闻官军收河南河北的那种“初闻涕泪满衣衫”的喜极之情,居然兀自躲在一隅垂泪。在那边知青伙伴们艳羡的眼光下,我稍稍收拾好自己一点不多的衣物,便匆匆赶回了长沙。次日,便在母亲殷殷的叮咛中,乘上了东去浏阳大围山的汽车。
扛着从湘南农村带来的那套家什,我在盘旋曲析的山路上向上攀爬。路旁的松柏和不知名的植物在早春二月的寒风中漱漱作响,犹自穿着的棉衣下面的内衣却早己了无一根干纱了。虽居住湘南大山几年,住地却是大山脚下的平原地带,此次转点的兴隆生产队深隐在大围山中,唐人的“白云深处有人家”一类的诗句便在脑海中盘旋,内心不禁升腾起一种新奇的感觉,尽管以自己当时的狼狈祥子不免有“叫化子”吟诗的酸相。
好不容易将那段盘山路爬完,转过一片竹丛,便听到了鸡鸣狗吠之声。我知道目的地不远了。突地,我的耳畔响起人声:“是到兴隆去的吗?”侧脸一看,一个三十多的汉子扛着把锄头站在坳上。此人五短身材却显精壮,白皙的脸看去不像农人。他笑吟吟地做着手势,将我引向左边一条路,并且将我的行李抢过来扛在肩上,他叫出了我的名字。看得出,他对我的到来早有所闻。
他叫邱清云,是兴隆生产队负责政治宣传的副队长。在一个异常陌生的地方,遇到的第一个对你表示亲和的人,无论是谁,都会心生感激的。我跟随着他,走向了这次旅行的目的地:知青点。我其实是个羞涩的孩子,真要面对一个陌生的环境,我的心不免会突突地蹦跳。
二、岛上的邻居
大围山林区绵延数百里,是长沙城市最接近的一个山区,它具有山区最典型的特点:山峦起伏、林深树茂、风景秀丽、环境幽静。若干年后,这里被僻为供游人玩乐的著名景点,并没有出乎我的意料。当时我将它比作“岛”,仅仅是因为彼时心境所造。这个叫和平大队的地方共辖有十一个生产队,均隐藏于山林深处,仅仅是幼成所在的八队和我先就认识的金玲所在的二队座落在一处较平坦的河谷中。兴隆是第五生产队,其所处位置最高,条件也最差。长沙下到和平有五十多个男女青年,而落户在兴隆的则有七个。一路上,邱清云嘴巴不停地在给我介绍当地的风土人情、队里概况以及长沙知青的情况。令我稍感意外的是,这个生产队并未按照以往“男女搭配”的落户原则,仅有一位叫孙惠的女生下放在此,而且,他有一个男朋友刘苏民就在队上。其余,全是公的。哈,这下又来了个公的。
约半小时后,邱清云将我带到一排土筑墙构造的知青点前,介绍给兴隆几个知青的时候,他们竟然显示了一种不应有的冷漠,他们或者漫不经心点点头,或者在忙自己的事根本无视我的到来。这又让我感到了意外。以我下放湘南的经验,作为同属知青群体的人哪怕从未谋面,只要到了我那里,无论如何总是会很热情的。更让我惊愕的是,有个年纪稍大的据说是一位高中生,他叫“罐子”。他凝视我片刻说道:“你别住这里,住到外面去!”语气生硬,我似乎像一个不太受欢迎的人。而站在旁边的几位知青,有的露着你无法猜透的浅笑,有的好像在思考着什么,但没有一个插句言,或是有一言半句的喧寒问暖。我的到来似乎与他们无关。会不会是我的到来侵占了他们的什么?或是下放的地方离家太近,反而失去了亲近感?这是我以后相当长的时间还在考虑的问题。千真万确的是,来到兴隆的第一天,我便遭遇到了一种不能融入知青群体的冷遇,内心沮丧而尴尬,这是我始料未及的。很多年后,知青们都回到了城市,经常会在一起聚聚,大家都说:我们有相同的生活经历,有浓厚的“知青情结”,因此,我们的友情至死也不会改变。我承认这些话语有一定道理,也屡次被这些“情结”所驱动而愿意尽自己的绵薄之力。但是,为了还原当年的真实现场,我不能不如此秉笔直书
我至今还在感念那位叫幼成的女生。其实她是与弟弟同大队不同生产队的一位女知青。下乡不久,他们为了找条出路,不约而同地到大队凉席厂去学竹蔑工,于是就认识了。幼成的性格风风火火、敢作敢为,高喉咙大嗓子,颇有点男子的气慨,而弟弟的老实厚道、少言实干精神很快便羸得了她的好感。他们成了无话不谈的好朋友。记得他们有次一起回城,还带了些半成品竹蔑,俩人联手为两家各编织了一床精美适用的凉席。唯一可以断定的是,那种很保守的年代,他们之间的友谊并没有逾越那种男女之情。况且弟弟很清楚,像我们这样骇人听闻的家庭背景、太黑的政治出身,要和人家姑娘结缘,那是害了她。幼成却一如既往在我家走动却是令我们全家感动。顺理成章,这次我的转点便是她一手操办的。她与大队会计一家的关系比较好,原打算将我的户口迁到她所在的八队,但八队实在是人多田少,户口难以迁进,最后只好选择了条件比较差的兴隆五队,这也尽了她九牛二虎之力了。
当日夜晚,她闻讯从远在山坳那边的十一队赶来。带了点米和蔬菜,一边急急地为我清理东西、用报纸将四壁洞穿的地方补好,一边择菜煮饭、告诉我新来此地应注意哪些地方,别让人欺了生;特别要注意和队上的知青搞好团结,等等。临走,她又一再嘱咐:屋顶上那个洞会漏雨,等二天带你去剥二块杉皮盖上……
看着她消失在葱茏黑暗的山林中,心里不由生出了几许感激,白天的不快霎间消失了。
知青们早就各自为政地自己架起了炉灶,所以我也必须自己弄着吃,只是历来被女知青照顾惯了的我,做这些生活上的事显得笨拙。我的住处被安排在一处当风的山梁上,这是一座破烂不堪的茅草屋,住着我,也住着一个叫向胜的矮个知青。他说“罐子”也嫌弃他,他己经单独在这里住了一年多了。
这里的知青闹不团结、互相攻讦的情况甚至连当地老乡们都清楚。为了争一个大队民办教师的位置,他们可以“互揭老底”;为了哪个知青的底分比自己高一分,可以互不理睬,直至哪天动起粗来……面对此情此景,我实在感到困惑。我是“鸡里面插只鸭”,新来的。不能确定我能在这里呆到哪天,但我毕竟不能生活在一个孤独的真空里,我还得与他们打交道。我与他们没有宿怨,应该不存在“利害冲突”,我决定主动出击,用自己一点有限的才能和真诚的做人去溶化他们的冷漠。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与他们逐渐熟络了。首先是那一对同居的男女知青孙惠和刘苏民接近了我。孙惠是一位多愁善感的姑娘,常常莫名地落泪。来兴隆二个月了,我从没看到她出过一天工,但她有个特点:很爱看书。有一次看到她在阳光下的屋场上捧着一本书在看,有心与他们套近乎的我,便笑着与她打招呼,趋前拿起了这本书。这是陀思妥也夫斯基的《罪与罚》,我便与她谈起陀氏的好赌以及婚姻爱情生活。孙惠似乎很感新奇,便与我谈起了文学。她读过很多书,饶有兴致地说到普希金的诗歌,也说到文革前的一些小说。我是个喜欢读点书的人,特别对俄国文学,我是用近乎一种崇拜的心理来对待的。中国盛产诗歌,产生了李杜屈子这样的诗歌巨匠;俄罗斯则盛产小说,这些小说让我手不释卷、留连难返,我觉得俄罗斯是一个伟大的民族。我是从普希金、屠格涅夫等几位作家开始接触俄国文学的。少年时代认识的一位男老师,学的是中文专业,原本应该去教中学,可是在他大学毕业那年因参加了年级一个文学团体,而被打成了有反革命嫌疑的组织成员,幸亏后来学校“宽大处理”总算才保住了饭碗。最终分到我母亲所在的小学教书。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到他家下棋,让我有了与这些书籍谋面的机会。整个一暑假里,我贪婪地读完了《父与子》、《罗亭》、《安娜.卡列尼娜》、《复活》等文学名著。而陀氏的《赌徒》和《罪与罚》则是在开学以后借去陆续读完的。虽说在今后漫长跌宕的生活中,我早己失去了对文学的嗅觉,但陀氏作品中人物的怪诞和场面的惊心动魄、冲突和高潮的引人入胜还是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孙惠说到的这些小说和诗歌都是我读过的,有时不免就有些卖弄地高谈阔论起来。因了这些谈论书籍的接触,有次孙惠突然说了一句:“你还真有点像落拓的才子哩!”哈,我不当什么才子,我只想在这陌生的环境中尽早认识几个人,这才是我的真实目的。不过,孙惠的话却让我很受用,在泥泞中淌了很久的人,陡然听到本该在书斋中才能听到的话,我感觉到了一种亲切。可以断定的是,从此她那有些木纳的脸开始有了笑容,并且时不时还弄点酸菜、剁辣交送到我的饭桌上。
刘苏民乐意与我交往的原因并非是书籍,他只是个十足的粗人。那时,他也加入了“知青木匠”一流,不是当时对知青找出路有种讲法么:男学木匠,女学裁缝。我是从湘南大山里走出来的,在城市又厮混过好几年的“木工流”,自然有一手好的木工技术。一次,我见他在做一种园角型的二斗柜,便建议他采用平装板式的做法,这样看去显得更漂亮简洁。他接受了,但经过一番折腾后终不满意。我知道这是他工具不精、技术不过关的原因,便将带来的木工工具拿来,让他打下手,亲自上阵,用二天的时间便做出了一张里外精细、造型漂亮的二斗柜。竣工那天下午他叫来了除“罐子”以外的所有知识青年,他兴奋地大叫:“我要用这张柜子结婚,我真还看不出健哥有这祥的狠哩!”众知青个个围拢来,看看摸摸,一致称赞“柜做得精细!”当场,正在学木匠的四鳖提议要拜我为师。
无法言说的冷漠,深感寂寞的孤独。只有此刻我才感受到了一种靠近群体的温暖。几个月来一直在被冷漠隔绝了的我,心里顿时一热,直觉得眼泪模糊了双眼,我赶快扭过头去磨起了刨铁。
不能不提的那个人是“罐子”。与众不同的是,他高中毕业下的乡,年纪也稍大几岁,背后有一个很凄惨的身世。一双眼晴藏在厚厚的镜片后面,显得阴鸷,我的到来似乎一直就为他所排斥。几个年纪小一点的知青围着他转,将他当成了“精神领袖”。我不受“罐子”的礼遇,自然也不会被他们所接受了。然而随后爆发的一件事,却让这种冷漠的局面有了彻底的改变。那天,刘苏民捂着嘴在笑:你去看‘罐子’做的柜子,只怕就会散架!”颇有点嘲弄的意味。然而,我却在想是不是利用自己的一技之长来帮帮他,也好缓解一下彼此的关系,于是赶紧来到了“罐子”的住处。“罐子”正在按我给刘苏民做的柜样做,显然,由于他的技术太差,抽屉也做大了,“柜子”看去怪模怪样的。他早己经领教过我的技术,于是很虚心地向我讨教,而我认为只能废了重做了,他也依了我。用不到一天的时间,我很快便将柜架拼镶好,并答应他等几天再做柜子附件。
然而,令人意想不到的是,他对我的敌意并未稍减,还在暗地里挑拨我与刘苏民的关系。一次队里出工锄勘头草,刘苏民偷偷告诉我,“罐子”曾告诉他:“你屋里孙惠不要再和张某扯什么文学了,你别到时老婆被人家‘鸟’了,还为人家放鞭炮!”刘苏民还说:“他就是要孤立你,要让你像向胜那样没人理睬!”
如同火上加油,刘苏民一席话,让我怒不可遏。我做人的原则是:可以在物质上吃亏,但绝不允许人格受到玷污。于是提了把斧子,冲到“罐子”住处,在“罐子”和众人的惊愕之中,将那尚未完成的柜体一顿乱砍,而且,为了消恨将己成砍成碎片的木头堆到外面燃起了一团火……
扭曲年代滋生扭曲的性格,当人性无休止地被抑制时,人的心理会变得分外阴暗,对世间事物会形成极为荒诞的偏见从而产生一系列错误的应对。大约“罐子”正是这种人。很多年后,在想到“罐子”这人的时候,我是这样理解的。人的劣根性会给人带来冷漠、伤害,这次我的发怒也许伤害了“罐子”,但令人不解的是,也正是我的这次“不打不相识”的超常之举,让他们彻底认识了我。我与兴隆知青点的每个人都变得融洽起来,直至我离开大围山。
约半小时后,邱清云将我带到一排土筑墙构造的知青点前,介绍给兴隆几个知青的时候,他们竟然显示了一种不应有的冷漠,他们或者漫不经心点点头,或者在忙自己的事根本无视我的到来。这又让我感到了意外。以我下放湘南的经验,作为同属知青群体的人哪怕从未谋面,只要到了我那里,无论如何总是会很热情的。更让我惊愕的是,有个年纪稍大的据说是一位高中生,他叫“罐子”。他凝视我片刻说道:“你别住这里,住到外面去!”语气生硬,我似乎像一个不太受欢迎的人。而站在旁边的几位知青,有的露着你无法猜透的浅笑,有的好像在思考着什么,但没有一个插句言,或是有一言半句的喧寒问暖。我的到来似乎与他们无关。会不会是我的到来侵占了他们的什么?或是下放的地方离家太近,反而失去了亲近感?这是我以后相当长的时间还在考虑的问题。千真万确的是,来到兴隆的第一天,我便遭遇到了一种不能融入知青群体的冷遇,内心沮丧而尴尬,这是我始料未及的。很多年后,知青们都回到了城市,经常会在一起聚聚,大家都说:我们有相同的生活经历,有浓厚的“知青情结”,因此,我们的友情至死也不会改变。我承认这些话语有一定道理,也屡次被这些“情结”所驱动而愿意尽自己的绵薄之力。但是,为了还原当年的真实现场,我不能不如此秉笔直书
我至今还在感念那位叫幼成的女生。其实她是与弟弟同大队不同生产队的一位女知青。下乡不久,他们为了找条出路,不约而同地到大队凉席厂去学竹蔑工,于是就认识了。幼成的性格风风火火、敢作敢为,高喉咙大嗓子,颇有点男子的气慨,而弟弟的老实厚道、少言实干精神很快便羸得了她的好感。他们成了无话不谈的好朋友。记得他们有次一起回城,还带了些半成品竹蔑,俩人联手为两家各编织了一床精美适用的凉席。唯一可以断定的是,那种很保守的年代,他们之间的友谊并没有逾越那种男女之情。况且弟弟很清楚,像我们这样骇人听闻的家庭背景、太黑的政治出身,要和人家姑娘结缘,那是害了她。幼成却一如既往在我家走动却是令我们全家感动。顺理成章,这次我的转点便是她一手操办的。她与大队会计一家的关系比较好,原打算将我的户口迁到她所在的八队,但八队实在是人多田少,户口难以迁进,最后只好选择了条件比较差的兴隆五队,这也尽了她九牛二虎之力了。
当日夜晚,她闻讯从远在山坳那边的十一队赶来。带了点米和蔬菜,一边急急地为我清理东西、用报纸将四壁洞穿的地方补好,一边择菜煮饭、告诉我新来此地应注意哪些地方,别让人欺了生;特别要注意和队上的知青搞好团结,等等。临走,她又一再嘱咐:屋顶上那个洞会漏雨,等二天带你去剥二块杉皮盖上……
看着她消失在葱茏黑暗的山林中,心里不由生出了几许感激,白天的不快霎间消失了。
知青们早就各自为政地自己架起了炉灶,所以我也必须自己弄着吃,只是历来被女知青照顾惯了的我,做这些生活上的事显得笨拙。我的住处被安排在一处当风的山梁上,这是一座破烂不堪的茅草屋,住着我,也住着一个叫向胜的矮个知青。他说“罐子”也嫌弃他,他己经单独在这里住了一年多了。
这里的知青闹不团结、互相攻讦的情况甚至连当地老乡们都清楚。为了争一个大队民办教师的位置,他们可以“互揭老底”;为了哪个知青的底分比自己高一分,可以互不理睬,直至哪天动起粗来……面对此情此景,我实在感到困惑。我是“鸡里面插只鸭”,新来的。不能确定我能在这里呆到哪天,但我毕竟不能生活在一个孤独的真空里,我还得与他们打交道。我与他们没有宿怨,应该不存在“利害冲突”,我决定主动出击,用自己一点有限的才能和真诚的做人去溶化他们的冷漠。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与他们逐渐熟络了。首先是那一对同居的男女知青孙惠和刘苏民接近了我。孙惠是一位多愁善感的姑娘,常常莫名地落泪。来兴隆二个月了,我从没看到她出过一天工,但她有个特点:很爱看书。有一次看到她在阳光下的屋场上捧着一本书在看,有心与他们套近乎的我,便笑着与她打招呼,趋前拿起了这本书。这是陀思妥也夫斯基的《罪与罚》,我便与她谈起陀氏的好赌以及婚姻爱情生活。孙惠似乎很感新奇,便与我谈起了文学。她读过很多书,饶有兴致地说到普希金的诗歌,也说到文革前的一些小说。我是个喜欢读点书的人,特别对俄国文学,我是用近乎一种崇拜的心理来对待的。中国盛产诗歌,产生了李杜屈子这样的诗歌巨匠;俄罗斯则盛产小说,这些小说让我手不释卷、留连难返,我觉得俄罗斯是一个伟大的民族。我是从普希金、屠格涅夫等几位作家开始接触俄国文学的。少年时代认识的一位男老师,学的是中文专业,原本应该去教中学,可是在他大学毕业那年因参加了年级一个文学团体,而被打成了有反革命嫌疑的组织成员,幸亏后来学校“宽大处理”总算才保住了饭碗。最终分到我母亲所在的小学教书。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到他家下棋,让我有了与这些书籍谋面的机会。整个一暑假里,我贪婪地读完了《父与子》、《罗亭》、《安娜.卡列尼娜》、《复活》等文学名著。而陀氏的《赌徒》和《罪与罚》则是在开学以后借去陆续读完的。虽说在今后漫长跌宕的生活中,我早己失去了对文学的嗅觉,但陀氏作品中人物的怪诞和场面的惊心动魄、冲突和高潮的引人入胜还是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孙惠说到的这些小说和诗歌都是我读过的,有时不免就有些卖弄地高谈阔论起来。因了这些谈论书籍的接触,有次孙惠突然说了一句:“你还真有点像落拓的才子哩!”哈,我不当什么才子,我只想在这陌生的环境中尽早认识几个人,这才是我的真实目的。不过,孙惠的话却让我很受用,在泥泞中淌了很久的人,陡然听到本该在书斋中才能听到的话,我感觉到了一种亲切。可以断定的是,从此她那有些木纳的脸开始有了笑容,并且时不时还弄点酸菜、剁辣交送到我的饭桌上。
刘苏民乐意与我交往的原因并非是书籍,他只是个十足的粗人。那时,他也加入了“知青木匠”一流,不是当时对知青找出路有种讲法么:男学木匠,女学裁缝。我是从湘南大山里走出来的,在城市又厮混过好几年的“木工流”,自然有一手好的木工技术。一次,我见他在做一种园角型的二斗柜,便建议他采用平装板式的做法,这样看去显得更漂亮简洁。他接受了,但经过一番折腾后终不满意。我知道这是他工具不精、技术不过关的原因,便将带来的木工工具拿来,让他打下手,亲自上阵,用二天的时间便做出了一张里外精细、造型漂亮的二斗柜。竣工那天下午他叫来了除“罐子”以外的所有知识青年,他兴奋地大叫:“我要用这张柜子结婚,我真还看不出健哥有这祥的狠哩!”众知青个个围拢来,看看摸摸,一致称赞“柜做得精细!”当场,正在学木匠的四鳖提议要拜我为师。
无法言说的冷漠,深感寂寞的孤独。只有此刻我才感受到了一种靠近群体的温暖。几个月来一直在被冷漠隔绝了的我,心里顿时一热,直觉得眼泪模糊了双眼,我赶快扭过头去磨起了刨铁。
不能不提的那个人是“罐子”。与众不同的是,他高中毕业下的乡,年纪也稍大几岁,背后有一个很凄惨的身世。一双眼晴藏在厚厚的镜片后面,显得阴鸷,我的到来似乎一直就为他所排斥。几个年纪小一点的知青围着他转,将他当成了“精神领袖”。我不受“罐子”的礼遇,自然也不会被他们所接受了。然而随后爆发的一件事,却让这种冷漠的局面有了彻底的改变。那天,刘苏民捂着嘴在笑:你去看‘罐子’做的柜子,只怕就会散架!”颇有点嘲弄的意味。然而,我却在想是不是利用自己的一技之长来帮帮他,也好缓解一下彼此的关系,于是赶紧来到了“罐子”的住处。“罐子”正在按我给刘苏民做的柜样做,显然,由于他的技术太差,抽屉也做大了,“柜子”看去怪模怪样的。他早己经领教过我的技术,于是很虚心地向我讨教,而我认为只能废了重做了,他也依了我。用不到一天的时间,我很快便将柜架拼镶好,并答应他等几天再做柜子附件。
然而,令人意想不到的是,他对我的敌意并未稍减,还在暗地里挑拨我与刘苏民的关系。一次队里出工锄勘头草,刘苏民偷偷告诉我,“罐子”曾告诉他:“你屋里孙惠不要再和张某扯什么文学了,你别到时老婆被人家‘鸟’了,还为人家放鞭炮!”刘苏民还说:“他就是要孤立你,要让你像向胜那样没人理睬!”
如同火上加油,刘苏民一席话,让我怒不可遏。我做人的原则是:可以在物质上吃亏,但绝不允许人格受到玷污。于是提了把斧子,冲到“罐子”住处,在“罐子”和众人的惊愕之中,将那尚未完成的柜体一顿乱砍,而且,为了消恨将己成砍成碎片的木头堆到外面燃起了一团火……
扭曲年代滋生扭曲的性格,当人性无休止地被抑制时,人的心理会变得分外阴暗,对世间事物会形成极为荒诞的偏见从而产生一系列错误的应对。大约“罐子”正是这种人。很多年后,在想到“罐子”这人的时候,我是这样理解的。人的劣根性会给人带来冷漠、伤害,这次我的发怒也许伤害了“罐子”,但令人不解的是,也正是我的这次“不打不相识”的超常之举,让他们彻底认识了我。我与兴隆知青点的每个人都变得融洽起来,直至我离开大围山。
三、受伤的漂泊客
知青年代的爱情是奢侈的,这可以从无数对相恋的知青男女迭经不幸中得以佐证;知青时代的爱情又是不以人的意志可以阻挡的,它会如一朵灿烂的山花悄然绽放。我从湘南转点到大围山之前,那正是我感情世界受到巨大创伤的日子。一个比我稍大一点的女知青琴一直在默默地爱着我,无论冬夏总用她温柔的女性给我带来温馨和安慰,用她美丽的胴体疗治我心灵的痛苦,用她睿智的语言为我启明人生的去路。因此,我们相约:即便我们不能走出大山,我们就在大山中终生相伴终老。我们不知道,生活是严酷的,人的生命其实是具有社会属性的。往往自己的生命、自己的婚姻并不能由自己主宰的。琴在一次返城后,竟杳无音讯。在一年以后见到她的时候,她拿出了一沓转点证明,抱着我痛哭,她说她不能丢掉家庭,她只能舍弃自己的爱情。接着,琴的家庭、琴家人的朋友们为了彻底让琴与我断掉,采取了“转点”隔离,也动用了当时炙手可热的权势进行威胁。母亲来信:我们这样一个弱势的家庭是难以抵御强权政治的,你要我活,你就必须离开琴…
我明白,最纯真的初恋己经埋葬在大青山了;我明白,以我稚嫩的肩膀是无法对抗强大的社会惯力的。于是,我选择了理性。当然,这理性的选择是我付出三天三夜不吃不喝不眠不语的代价而获得的。琴,是我爱情的老师,也是我对人生方方面面得到更深体悟的“催化剂”。很多年过后,我在回忆当年那种情景仍会惊奇自己的定力。一个人在感情上受到重创后,总会有相当长的沉寂期,心如死灰,心如止水。这是一种很可怕的疾病,它让一个对世界充满美好憧憬的年轻人对世界扭曲化、妖魔化,会否认人世存在真情实感,会拒绝男女的爱情,一切是虚幻的,一切是避凶趋吉的功利行为。假如一个人长久浸渍在这种充满毒汁的冥想中,他的生命无可药救。如同一位深陷重疴的病人,在拼死寻觅自救的良药,而大围青山的秀丽,山中流泄的清泉正如同一位圣手名医在医治我的创伤,使我得以迅速平复,掩埋好自己死去的过去,重新上路。我至今感叹:大围山是我生命中重要的一个驿站。
我明白,最纯真的初恋己经埋葬在大青山了;我明白,以我稚嫩的肩膀是无法对抗强大的社会惯力的。于是,我选择了理性。当然,这理性的选择是我付出三天三夜不吃不喝不眠不语的代价而获得的。琴,是我爱情的老师,也是我对人生方方面面得到更深体悟的“催化剂”。很多年过后,我在回忆当年那种情景仍会惊奇自己的定力。一个人在感情上受到重创后,总会有相当长的沉寂期,心如死灰,心如止水。这是一种很可怕的疾病,它让一个对世界充满美好憧憬的年轻人对世界扭曲化、妖魔化,会否认人世存在真情实感,会拒绝男女的爱情,一切是虚幻的,一切是避凶趋吉的功利行为。假如一个人长久浸渍在这种充满毒汁的冥想中,他的生命无可药救。如同一位深陷重疴的病人,在拼死寻觅自救的良药,而大围青山的秀丽,山中流泄的清泉正如同一位圣手名医在医治我的创伤,使我得以迅速平复,掩埋好自己死去的过去,重新上路。我至今感叹:大围山是我生命中重要的一个驿站。
四、感受景致
在结束了一天农耕的劳累后,我喜欢倚窗凝视着外面的景色,我看到在渐近的暮色中,细雨连绵、群山朦胧,山脚下的小河穿山过峡静静地流向远方。如此日复一日的劳作,并未体现多年后所讲的那种“经济效果”,生命在消失,时间却在静止,没有书籍阅读、没有日历,人的嘴仅仅用在每日三餐的嚅动上,人的耳仅仅用在谛听山林的呼啸声上,人的生命意义何在?所有“业余”时间要么与同屋的向胜闲扯几句,更多的时间却是窝在被子里想些无意义的心思。这几天,晒谷坪里架着的大喇叭不断地重复广播着毛主席给李庆林的复信:“……寄上三百元,聊补无米之炊。”似乎离我很遥远,与自己无关,也未给自己带来更多的兴奋点。我的生命如同山脚下那条小河,在阳光下如泪水般地闪着光,然后经过千回百折消失在群山之中,我的生命不正像这条小河吗?童年、少年所拥有的那些五彩斑斓的梦想,恐怕只有来生再见了。曾经是个富于梦想的孩子,但我至今认识到的人生竟会有如此的残酷,我叹息自己生命的可怜!
下放在二队的金玲,原一中的高中毕业生,文理两精,才华横溢,以至于若干年后我闻听她担任市某局的一把手,一点也不感觉奇怪。但那时,她在大队小学担任民办老师。早在知青大返城的时候就认识她,缘于一次她随我弟弟来家,正好看见我在练书法,对我写的几个字大加赏识,而她是个对文化很敏感的人。也许她有那么点“惺惺相惜”的心情,自我转点到兴隆后,一直受到她很多的帮助。侍弄一天的孩子后,己经极感疲惫的她,总会时不时顶着月光孤身爬上山来帮我清理个人卫生、或是为我带一点菜送几本书等等,尤其让我感动的是,由于金玲很多次的造访甚至与我的几次秉夜长谈,己引起一些人的非议,但她却不管不顾,特立独行。与我几次交谈了解我正陷入苦闷后,即连续不间断地上门陪我聊天、谈文学、谈人生。客观上,我能平安地度过自己一生来最大的精神低谷期,金玲的帮助功不可没。人们常常为“男女之间有不有友谊?”的话题而无休止地进行争论,以我的人生经验:不否认男女之间那种异性相互的吸引,相互的崇拜,但在那特殊的年代里,这种特殊的友情化解着风雪的侵袭,成为冰山上的一朵雪莲。我要说:男女友谊的存在是不容争辩的。
金玲于九十年代己移居深圳,早己有了一个幸福的家庭,境况甚好,这让我感到欣慰。我走笔至此向南天遥祝:好人一生平安!
下放在二队的金玲,原一中的高中毕业生,文理两精,才华横溢,以至于若干年后我闻听她担任市某局的一把手,一点也不感觉奇怪。但那时,她在大队小学担任民办老师。早在知青大返城的时候就认识她,缘于一次她随我弟弟来家,正好看见我在练书法,对我写的几个字大加赏识,而她是个对文化很敏感的人。也许她有那么点“惺惺相惜”的心情,自我转点到兴隆后,一直受到她很多的帮助。侍弄一天的孩子后,己经极感疲惫的她,总会时不时顶着月光孤身爬上山来帮我清理个人卫生、或是为我带一点菜送几本书等等,尤其让我感动的是,由于金玲很多次的造访甚至与我的几次秉夜长谈,己引起一些人的非议,但她却不管不顾,特立独行。与我几次交谈了解我正陷入苦闷后,即连续不间断地上门陪我聊天、谈文学、谈人生。客观上,我能平安地度过自己一生来最大的精神低谷期,金玲的帮助功不可没。人们常常为“男女之间有不有友谊?”的话题而无休止地进行争论,以我的人生经验:不否认男女之间那种异性相互的吸引,相互的崇拜,但在那特殊的年代里,这种特殊的友情化解着风雪的侵袭,成为冰山上的一朵雪莲。我要说:男女友谊的存在是不容争辩的。
金玲于九十年代己移居深圳,早己有了一个幸福的家庭,境况甚好,这让我感到欣慰。我走笔至此向南天遥祝:好人一生平安!
《未完待续》